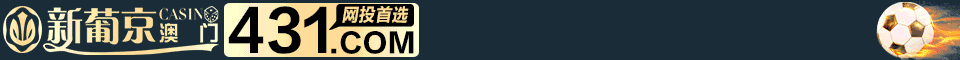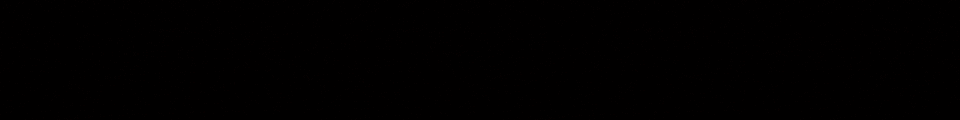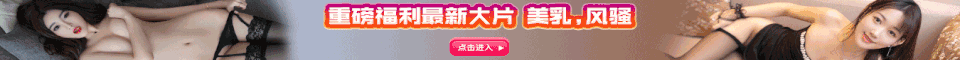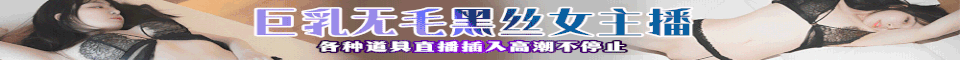百妇谱 全本-9
“去,”一听到这里,文君小姐一撇小嘴:
“竹竿何枭枭,鱼尾何蓰蓰。
男儿重意气,何用钱刀为。”
“姐姐,如不是那个意思,如是说,无论什么事情,如都听姐姐的,”
“唉,”美人又饮习一杯,放下着空酒杯,美人泪眼凝望着窗外,手抚着古琴,深有感触地说道:
“春华竞芳,五色凌素,琴尚在御,而新声代故。锦水有鸳,汉宫有水,彼物而亲,嗟世之人兮,瞀于淫而不悟。”
“谢谢姐姐教诲,如永志不忘,”司马搬过古琴,讨好道:“如果姐姐想听,如现在就弹上一曲!”
“算了吧,”文君小姐手指一拨,一根琴弦叭地折断:
“朱弦断,明镜断。朝露希,芳颜歇。白头吟,伤离别。”
“姐姐,你,”司马怔怔在望着断弦,文君叹了口气,以长辈的身份拍了拍司马的肩膀:
“唉,努力加餐毋念妾。锦水汤汤,与君长诀!”
言罢,文君小姐转身走出餐厅,司马扔掉古琴,急切切地尾随而去,王某站在门口,冷冷地瞅着司马:“偶像,这是何苦啊,难道天底下的女人都死绝了,没有她你活不了哇?”
“你懂个什么!”相如没有理会王某,看见文君跳上马车,扬起马鞭,司马健步上前,纵身而上,文君淡然而道:“你上来做啥?你知道我去哪啊!”
相如与文君并肩而坐:“姐姐,无论你到哪里,如永远跟着你!”
一首白头吟感动了风流才子,让司马相如死心塌地的投入文君的怀抱,直至终老,成为千古佳话。司马先于文君而去,扣上司马相如的棺盖,文君为夫君,同时也是为自己写下最后的定论:
嗟吁夫子兮,禀通儒;小好学兮,综群书。纵横剑技兮,英敏有誉;尚慕往哲兮,更名相如。落魄远游兮,赋子虚;毕尔壮志兮,驷马高车。忆初好兮,雍容孔都;怜才仰德兮,琴心两娱。永托为妃兮,不耻当炉;平生浅促兮,命也难扶。长夜思君兮,形影孤;步中庭兮,霜草枯。雁鸣哀哀兮,吾将安如!仰天太息兮,抑郁不舒;诉此凄恻兮,畴忍听余。泉穴可从兮,愿捐其躯。
「妇谱氏曰」
妻者,齐也,或德或才或貌,必有一相配而后谓齐也。司马相如此生若不偶识卓文君,则绿绮之弦俱废;而文君不遇相如,芳颜芙丽,后世亦不复有传颂者。是妇是夫,千秋为偶。风流放诞,岂可瑕也!以至今日之山东地区,唐谓之相如县;迄今有相如祠。相如之后代若此!彼风流放诞者得乎哉。
文君之为人,放诞风流也。女不侠,不豪;侠不放诞风流,不豪;放诞风流不色姣好,不豪;姣好放诞,所私奔若非如相者也,亦不豪;奔相如不家徒四壁,亦不豪;家徒四壁,不亲当炉,涤器于市,亦不豪;亲当炉,又不得僮百人,钱百万,太守郊迎,县令负驽,卓王孙、临邛富人等皆伛偻门下,亦不豪;此所以为放诞风流也。文群以身殉相如,相如亦以身殉文君,一琴一诔,已足千古也。
殉妇
《百妇谱》之
(谱壹拾捌)
清平乐。殉妇
家贫无福,人贱休谈禄。
敢问何方能享福,请到穹苍籁竺。
花妮绝食身亡,换来一栋牌坊。
牌坊庄中耸立,赚得爹爹官装。
第一回酒鬼丈夫烂醉渲淫,一通狂射精中带血
今生今世最爱酒,从早到晚不离手。
痛饮一樽豪情壮,连干二碗精神抖。
推杯换盏行酒令,拳来脚去狂斗殴。
稀里哗啦尿裤裆,翻江倒海喷出口。
花妮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会嫁给一个嗜酒如命丈夫,十里八村的乡邻们都称之为“酒鬼”。
新婚的那一天,披红戴花的新郎官陪客人饮酒,一桌酒席尚未陪完,客人尚未尽兴,酒鬼丈夫自己则醉倒了,被众人四脚朝天地抬进洞房里,咕咚一声扔在热滚滚的土炕上。
花妮从红盖头的下沿悄然望去,只见新郎官一动不动、仰面朝天的躺在土炕上,周身酒气升腾,很快便响起如雷的鼾声。
随着酒宴的继续进行,厨间的炉灶一刻不停地燃烧着,烟道与新房相连的土炕温度越烧越高,渐渐地新娘子嗅闻到一股呛人的腥骚闻,花妮大惊:“不好,夫君要烤糊喽!”新娘子等不及新郎官来揭盖头,自己掀到一旁,慌忙爬到酒鬼丈夫的身旁,一把揪住酒鬼的身子,急促地摇晃起来:
“快醒一醒,换个位置再睡,你的背脊都要烤焦了!”
酒鬼依然一动不动,仿佛死了一般,花妮只好用力推动着酒鬼,感觉新郎官虽然身躯庞大,体重却是极轻:这家伙,年纪轻轻,而身子则让烈性酒精给烧成一把柴炭了!花妮绝非危言耸听,大凡常年酗酒之人,其结局无不面黄肌瘦,体轻如柴,若果不加节制地继续酗酒,身体便慢慢地萎缩起来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佝偻症。
新娘子玉手稍一用力,便非常轻松地将酒鬼翻过身去,呼——登时,一股灼面的热气直扑花妮的面庞,新娘子顾不得因陌生而萌发的羞涩感,立刻给酒鬼丈夫宽衣去裤,烛光下,酒鬼丈夫的背脊因长时间受火炕的烤灼,呈着深沉沉的暗红色,如果不是花妮及早发现、及时改变体位,新婚之夜,烂醉的酒鬼新郎官没有做成,却被火炕烙成肉饼了。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花妮的手心突然触到一片骚咸咸的潮湿,定睛一瞧,好么,酒鬼丈夫好生有出息,居然喝得尿了裤裆:“夫君啊,”新娘子手拎着酒鬼丈夫湿漉漉、骚哄哄的裤子,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:“你再这样不知深浅地喝下去,纵然不喝死,也得喝成瘫子,待油枯灯尽之后,慢慢地死掉!”
新娘子的推断不是没有依据的,花妮的表哥也是远近闻名的大酒鬼,几年前开始尿失禁,今年三十岁方才出个小头,已经瘫痪在床了,身子日渐枯萎,用舅母的话说:他啊,待这点心血耗光之后,便万事大吉喽!
“渴啊,”给酒鬼去光了衣裤,压好被子了,花妮正待睡去,酒鬼突然嚷嚷起来:“渴啊,水,水啊,我要喝水啊!”
“来喽,来喽,”花妮急忙下炕,哗地舀起一瓢凉水递到酒鬼的面前,酒鬼瞪着红通通的醉眼,双手捧过大木瓢,咧开嘴巴,咕噜咕噜地、仿佛饮牛一般地狂灌起来。
“咳咳咳,咳咳咳,”也许是喝得太急了,也许是灌得太猛了,酒鬼突然剧烈地干咳起来,旋即推开水瓢,扑地吐出一口粘痰来:
“啊,渴死我了,渴得我嗓子好紧、好咸啊!”
“哎呀,”望着地上的痰泡,花妮惊呼起来:
“夫君,你已经喝出毛病了,痰中带血啊!”
“没关系,”新郎官抹了一把嘴唇上的水珠,不以为然地笑道:“没什么大不了的,老毛病了,酒喝多了就犯,把酒停下几天就好了!”说毕,酒鬼丈夫冲新娘子会心地淫笑一番,一把将花妮揽进被窝里。
花妮咯咯一笑:“瞅你瘦得骨包骨头,真没想到,还蛮有些气力呢!”
“嘿嘿,”酒鬼丈夫终于清醒了几分,笑嘻嘻地搂住新娘子:“亲爱的,我虽然表面看着又干又瘦的,可是,气力不逊他人,尤其是这方面,”说到此,酒鬼大大咧咧地将手掌探进花妮的胯间:“肥猪乃蠢货,瘦马配良种,我人瘦,可是本事大,亲爱的,你信不信?”
“呵呵,”花妮也顺势握住了酒鬼丈夫的小弟弟:“喝了这么多的酒,你还行么?”
“我,”酒鬼丈夫信心十足,“咚”的将花妮按在身下,挥枪翻到新娘子的身上:“你不知道,老子酒喝得越多电越足!”
虽然喝得抽筋扒骨,痰中带血,结婚之后,酒鬼丈夫非但没有把酒停下来几天,反倒变本加厉了,天天必饮,顿顿皆喝,每天早晨扒开眼睛便开始饮酒,新婚的花妮不便过份劝阻,只好委惋地求助于婆婆:“夫君的酒喝得太甚了,长此下去,会把身子喝坏的!”
“唉,”婆婆双手一摊,露出一副无奈之相。
“我的好媳妇啊,婆婆前世没做好事,积下这么个孽缘来,大概是我前世欠他些什么,生出这个么讨债鬼来,四岁那年,他姨妈娶儿媳妇,我抱着他去参加婚礼,酒席上,这七大姑八大姨的,你一口、他一口的逗他玩,左一口、右一口的耍弄他。结果啊,这一来二去的,就把我儿子给灌醉了,你猜怎么着?回到家里,我儿大哭大叫,满土炕的打滚,好不容易把他哄睡了。”
“第二天醒来,还要喝那马尿,我不给,他就哭,宁可不吃奶水,也要喝那马尿,唉,我没辙了,就弄来一瓶,兑上清水哄他,从此以后啊,就、就完喽,小小年龄就把大酒给练成了。我也板过他,不给他酒喝,可是不成啊,这小子一天没有酒喝,就好似大烟鬼没有大烟泡抽一样,馋得抓心挠肝,撕衣揪发,掀桌子砸碗,甚至,甚至……”
说到此,婆婆面呈难色:“媳妇啊,不怕你笑话,这个逆子啊,实在鳖得急了,就耍混了,甚至、甚至……在我的面前挥拳踹脚,活生生要打他亲娘啊。乖乖,媳妇啊,你说,这不前世积的孽怨么,我活生生地养了一个畜生啊,瞅那架式,我若再不让他喝,他的拳头当真就能落在我的脸上啊。他爹死得早,我一个妇道人家又降不住他,我又能怎么办呢?唉,”婆婆长叹一声:
“这个生疔玩意啊,他愿意怎么喝就怎么吧,我也不管了,我也管不了,我拿他算是彻底没辙了!”
“嗨——”听罢婆婆的讲述,花妮懊悔不迭,亦是一声长叹,心中暗暗嘀咕道:“父亲这是怎样给女儿相的亲啊!仅听媒婆一面之词,也不托人好生探访探访,便如此草率地将女儿嫁给一个酒鬼,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?”
既然已经练成酒鬼了,当然就具备职业喝手的水平了,大凡一个合格的酒鬼饮酒时,无需什么象样的佐酒菜:一条青瓜;十余颗五香花生米;半块豆腐便能喝光一海碗老白干,当寒冷的冬天来临时,万物萧疏,餐桌上的菜肴历历可数,而职业酒鬼全然不在乎这些,几块硬生生、凉哇哇的白菜帮子就可以心满意足地痛饮一场。
而花妮的酒鬼老公,有据可查的最佳纪录是:半个橘子喝掉了一斤二锅头!
俗话说: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!既然爹爹给自己选择了一个酒鬼夫君,花妮也只能认命了,不认命又能如何啊?这又能怪谁呢?要怪只能怪自己前世没做好事,今世生就了女儿之身!花妮虽然没有念过书,却也知道三纲五常,知道女人应该尊敬翁婆、伺候丈夫。
既然丈夫喜欢饮酒,家中再怎么清贫,也要尽可能地给夫君搞些佑酒的菜,以免身体继续这样地干枯下去:“老公,不能这样喝,”看见酒鬼嚼一口大葱,喝一大口酒,花妮心痛地劝阻道:“酒和葱都是生热的玩意,你这样热上加热,会把胃肠烧坏的,你先别喝了,等我把这只猪耳朵给你切了,再就着酒喝吧!”
酒鬼丈夫无菜佐酒时,喝得却也畅快,谁知贤慧的媳妇搞来了下酒菜,一大年也未曾闻生命,在下深表敬佩,”说到此,周郎中拱了拱双手,然后,以开导的口吻道:“老太太的精爷我,我,”柯老爷嗖地抽剑出鞘,恶狠狠地压在徐氏的脖子上:“砍掉你的脑袋,就仿佛杀只小鸡,而我上呈的材料中,只要写明你不安心工作,一切便结了,懂么?”
徐氏的哭声嘎然而止,柯老爷的话绝对不是吹牛,更非言过其实,不久前,总是倚在窗前观望的徐氏,亲眼看见柯老爷手刃了一个不安心做苦役的囚犯,真尤如杀了一只小鸡。徐氏确信,柯老爷说得出来,就能做得到,为了活下去,为了能够与爱人团圆,徐氏不得不止住了悲泣,将悲伤深深地埋进心田。看见徐氏不哭了,也不闹了,柯老爷呛啷一声宝剑入鞘,坐到徐氏的面前:“唉,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,他,他有什么让你如此依恋的,难道,我就得不到你的真情么?说,”柯老爷端着徐氏的下巴:“还想不想他了?”
“不想!”
“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小妾?”
“愿意!”
“哼,”柯老爷一把推开徐氏:“全是他妈的假话,敷衍人的假话,啊,”既然永远也得不到徐氏的真情,而徐氏的身体却是顺手拈来,只要一看见徐氏妖娆的身段,柯老爷便性致昂然,他一边松解着徐氏的裤带,一边由衷的感叹着:“你的心,我永远、永远也得不到了,只有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啊!”
于是,柯老爷搂着徐氏,在昏暗的烛光下,哼哼呀呀地折腾起来,徐氏则紧闭着双眼,很不情愿地迎接着柯老爷的冲击,娇艳的胴体随着飘眇的烛光,时尔忽上,时尔忽下,望着反射在墙壁上的折影,望着摇动的幔帐,柯老爷总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,在他的身后,仿佛有一个甩不掉,躲不开的阴影:他妈的,柯老爷确信,那阴影便是许三:你他妈的人是走了,阴魂却是不散啊,唉,看起来啊,你小子的阴影,将永远笼罩住老爷我的房间里,在我与徐氏之间,形成一道虽然看不见,却是厚重无比的隔断。
“老爷,”柯老爷正满腹心思地享受着徐氏的胴体,馆外突然嘈杂起来,有心腹的衙役急切地呼唤着柯老爷:“老爷,不好了,我们抓到一个剌客!”
“什么,”柯老爷大叫一声,咚地从徐氏身上跳了下来,慌忙披上睡衣,推门而出:“剌客,剌客在哪?”
“在这,”黑暗之中,巡夜的兵卒将一个汉子推到柯老爷面前:“就是他,不知何时潜入老爷的馆舍,鬼鬼祟祟地徘徊在老爷的窗下,我们观察他许久了,看见他居然蹬上了窗户,我们估摸着他大概要入室行剌了,就立刻动手,将其擒拿住,请老爷亲自过堂审讯他吧!”
“啊,”借着月光,柯老爷眨巴着昏花的老眼仔细一看,所谓的剌客,原来是自己白天才打发走的许三:“许三,原来是你,你,你他妈的不回老家去,到老爷的舍内想什么魂?”柯老爷心里比谁都清楚,许三想什么魂?当然是徐氏的魂啊!听了柯老爷的斥问,许三可怜兮兮地垂下头去,同时,掏出一只口袋,递向柯老爷,夜风袭来,袋里叮当作响,那是银子相撞发出的声响:“老爷,这银子,我不要了,我要我的老婆!”
“混蛋!”柯老爷大骂一声,盛怒之下,居然耍起了孩子脾气:“你想要,我偏偏不给,气死你,馋死你!左右,”
“在,”
“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打入牢内,明天我再收拾他!”
“是,”
左右将许三推下,许三依然苦苦地乞求着,柯老爷理也不理,忿然返回舍内,一夜无话。
第二清晨,柯老爷余怒未息,依然耍小孩子脾气,你许三不是想要老婆么?我非但偏偏不给,还要你天天能看得见她,让你看着自己的老婆是如何伺候我的,让你难堪,让你伤心,于是,柯老爷令左右打了许三一通板子,故意将其安排在舍内打杂,令徐氏不得走出寝室一步,否则,杀无赦,斩立绝。
每天早餐后,许三估计着柯老爷应该升堂审案去了,便停下手中的活计,痴呆呆地伫立在柯老爷馆舍的门前,双眼直勾勾地射向窗扇,而徐氏则撩起窗幔,依窗与汉子默默相望,彼此间用目光交谈着、倾述着。
心腹的衙役早就将这些情形反应给了柯老爷,与往常的情况不同的是,柯老爷并没有暴跳如雷,更没有破口大骂,闭堂之后,刷刷地写了一通请柬,然后差人发往各处:原来,柯老爷今天六十岁大寿,要请客欢宴。
清天大老爷六十寿诞,谁人不敢前来贺寿啊,酒席之上,推杯换盏之余,看见许三与众仆人端着盘子,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,柯老爷抿着嘴唇嘿嘿冷笑一声,冲左右使了一个眼色,心腹衙役立刻俯首帖耳到柯老爷耳畔:“老爷有何吩咐?”
“嘿嘿,去,”柯老爷一脸神秘地说道:“把徐氏唤来,老爷我要与她喝几杯!”
“是,”
左右得令退下,徐氏很快出现在酒席桌前,恰巧与许三撞个满怀,众人哗然,无不以异样的目光扫视着这对被柯老爷强行拆开的恩爱夫妻。柯老爷见状,啪的一拍桌子,徐氏慌忙躲开许三,而许三也知趣地托着空盘子,从徐氏的身旁溜出宴会厅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徐氏很不自然地走向柯老爷,柯老爷又是一番嘿嘿的冷笑,示意徐氏坐到自己的身旁。此时,许三又返回餐厅内,手中端着盛满菜肴的盘子,眼睛却牢牢地盯着柯老爷身旁的徐氏,柯老爷见状,一把揽过徐氏,就在众人面前,很是大方地啃吮着徐氏面红似火的脸蛋:“爱——卿,”但见柯老爷搂着徐氏,旁若无人地做出种种轻佻的举动,众人看在眼里,心里都清楚:柯老爷这是故意做给许三看的:“啊,”柯老爷甚至将手掌探进徐氏的酥胸里,肆意抚弄起来:“好肥实的大奶子啊,真是养手啊,令人越摸越爱摸啊,呵呵,”
“嗯,”徐氏无地自容地依在柯老爷的怀里,难为情地闭上眼睛。柯老爷一边摸着、一边啃着,一边问道:“爱不爱老爷啊!”
“爱!”
许三看在眼里,一颗心在淌血,端着盘子的双手,瑟瑟发抖,看见自己心爱的人,被他人肆意轻佻,许三恨不得挥起手中的盘子,无情地砸向情敌——柯老爷。柯老爷丝毫也不在乎,大大咧咧地端过一只酒杯,塞到徐氏的手上:“嘿嘿,既然爱我,就请喝一樽交杯酒吧,嘿嘿,”
“是,老爷,请,”徐氏接过酒杯,不待与老爷碰杯,脖子一仰,咕噜一声灌进嘴里,辣得小嘴直咧,呛得泪珠乱窜,趁着老爷仰脖干杯之际,徐氏突然闭开双眼,表情极为复杂地扫视着餐桌对面的许三。
“啊,好酒!”柯老爷放下空酒杯,吧嗒吧嗒厚嘴唇,一手搂着徐氏的粉颈,一手指着餐桌对面的许三:“实话告诉老爷,你还爱他么?”
“这,”徐氏哑然,不知如何作答:“这,这,”徐氏吱唔了半晌,突然扬起面庞,壮着胆量,真诚地说道:“爱——!”
“哇——,”徐氏此言即出,举座皆惊,大家的目光纷纷转向柯老爷,不知难堪之下的官老爷如何收拾这个始终不回心转念的小妾。柯老爷放下酒杯,扫视一番四周,又咄咄地逼视着许三,而徐氏突然胆怯起来:“老爷,我说错了,我,我,”
“不,”柯老爷缓缓地站起身来:“你没说错,你说的是真心话,唉,”柯老爷已经有几分醉意了,又经徐氏这番嘲弄,渐渐有所顿悟,只听醉汉结结巴巴地言道:“古人云:宁拆一座坟,不拆一个婚,强拧的瓜不甜,既然徐氏的心里始终装着自己的原配丈夫,我从中作的什么梗啊,”
“老爷言之有理,”众人皆赞:“老爷不愧是京城来的大官,听了老爷这番话,在下胜读十年书啊!”
“所以,”众人的奉承,听得柯老爷飘飘然了:“左右,”
“在,”
“备马,送许三、徐氏回老家!”
“老爷,这,”左右茫然了:“老爷此话当真?”
“谁跟你们开玩笑呢?”
“谢谢老爷!”
徐氏扑通一声跪倒在柯老爷的脚下,许三见状,将托盘放在餐桌上,绕过餐桌,来到柯老爷面前,也一脸感激地跪了下来:“谢谢老爷!”
“唉,”柯老爷摆了摆手,说出来的一句话,把大家都逗乐了:“趁着本老爷尚未清醒之前,你们小两口还不快快离开此地,回家好生过日子去!”
「妇谱氏曰」
一个弱女子,因丈夫获罪而受牵连,在遥远的边关服苦役,不仅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,且不攀附权贵,不阿谀官僚,更不嫌弃窝囊的丈夫,虽然委身于官老爷,心中仍旧思念着结发的丈夫,其忠贞之心诚可叹也。现实生活中,莫说丈夫因罪入狱,往往因丈夫没有本事,赚不到钱,老婆便一拍屁股走人喽!
贵妇
《百妇谱》之()
《百妇谱》之
贵妇
(谱玖)
钗头凤•我爱表姐。
红脸蛋,白细手,婀娜妖身似杨柳。
春风绿,芳姿绰,心中挚爱,嘴上乞索。
摸,摸,摸!
空思念,为人妇,家境寒,貌奇丑,白天鹅,粪池落。
故人已去,旧情难却。
愕,愕,愕!
第一回调皮鬼想当小女婿,大美人不做唐惠仙
我家表姐初长成,面容姣好体轻盈。
提前一载登金榜,才貌双全满楼倾。
我的大表姐——毛毛,生得特别漂亮,真的,我今天没喝,头脑很清醒。大表姐的漂亮绝对不是我自己吹嘘出来,那是整个宿舍楼里公认的。当我还是一个抹着大鼻涕、满宿舍楼里调皮捣蛋的混噩顽童时,毛毛大姐已经出落成一个身材高佻、肌白肤嫩的婀娜小美人了。她就读于很是著名的省实验中学,每天放学时,走进宿舍楼的大院子,看见满脸灰土、浑身泥浆的我,大表姐不禁秀皱紧锁,厥着小嘴喋喋不休地训斥着我:“你瞅你弄得,哪里还有点人样啊,走,跟姐姐回家去,姐姐给你洗一洗!”
表姐一边嘟哝着,一边伸过细白的小手,模仿着舅妈的神态,像个小大人似地拧着我的耳朵。望着表姐那苗条的腰身,扭来扭去的丰臀,我一边佯装痛疼地、哎哟哎哟地尖叫着,一边高高地举起手中的黄泥,狠狠地抛掷在水泥地板上,只听叭的一声脆响,黄泥炮遍地开花,星星点点的泥浆溅在毛毛姐曲线优美、起伏不平的胸脯上,吓得她立刻松开细手,妈呀一声怪叫,连拍打身上的泥浆都顾不得,便连蹦带跳地落荒而逃了。
俏丽的大表姐是我的骄傲,而捉弄娇里娇气、柔声细语的小美人,也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摔够了泥泡,玩腻了玻璃球,我又逮住一只无家可归,在走廊的暖气沟里栖身的流浪猫仔,
“竹竿何枭枭,鱼尾何蓰蓰。
男儿重意气,何用钱刀为。”
“姐姐,如不是那个意思,如是说,无论什么事情,如都听姐姐的,”
“唉,”美人又饮习一杯,放下着空酒杯,美人泪眼凝望着窗外,手抚着古琴,深有感触地说道:
“春华竞芳,五色凌素,琴尚在御,而新声代故。锦水有鸳,汉宫有水,彼物而亲,嗟世之人兮,瞀于淫而不悟。”
“谢谢姐姐教诲,如永志不忘,”司马搬过古琴,讨好道:“如果姐姐想听,如现在就弹上一曲!”
“算了吧,”文君小姐手指一拨,一根琴弦叭地折断:
“朱弦断,明镜断。朝露希,芳颜歇。白头吟,伤离别。”
“姐姐,你,”司马怔怔在望着断弦,文君叹了口气,以长辈的身份拍了拍司马的肩膀:
“唉,努力加餐毋念妾。锦水汤汤,与君长诀!”
言罢,文君小姐转身走出餐厅,司马扔掉古琴,急切切地尾随而去,王某站在门口,冷冷地瞅着司马:“偶像,这是何苦啊,难道天底下的女人都死绝了,没有她你活不了哇?”
“你懂个什么!”相如没有理会王某,看见文君跳上马车,扬起马鞭,司马健步上前,纵身而上,文君淡然而道:“你上来做啥?你知道我去哪啊!”
相如与文君并肩而坐:“姐姐,无论你到哪里,如永远跟着你!”
一首白头吟感动了风流才子,让司马相如死心塌地的投入文君的怀抱,直至终老,成为千古佳话。司马先于文君而去,扣上司马相如的棺盖,文君为夫君,同时也是为自己写下最后的定论:
嗟吁夫子兮,禀通儒;小好学兮,综群书。纵横剑技兮,英敏有誉;尚慕往哲兮,更名相如。落魄远游兮,赋子虚;毕尔壮志兮,驷马高车。忆初好兮,雍容孔都;怜才仰德兮,琴心两娱。永托为妃兮,不耻当炉;平生浅促兮,命也难扶。长夜思君兮,形影孤;步中庭兮,霜草枯。雁鸣哀哀兮,吾将安如!仰天太息兮,抑郁不舒;诉此凄恻兮,畴忍听余。泉穴可从兮,愿捐其躯。
「妇谱氏曰」
妻者,齐也,或德或才或貌,必有一相配而后谓齐也。司马相如此生若不偶识卓文君,则绿绮之弦俱废;而文君不遇相如,芳颜芙丽,后世亦不复有传颂者。是妇是夫,千秋为偶。风流放诞,岂可瑕也!以至今日之山东地区,唐谓之相如县;迄今有相如祠。相如之后代若此!彼风流放诞者得乎哉。
文君之为人,放诞风流也。女不侠,不豪;侠不放诞风流,不豪;放诞风流不色姣好,不豪;姣好放诞,所私奔若非如相者也,亦不豪;奔相如不家徒四壁,亦不豪;家徒四壁,不亲当炉,涤器于市,亦不豪;亲当炉,又不得僮百人,钱百万,太守郊迎,县令负驽,卓王孙、临邛富人等皆伛偻门下,亦不豪;此所以为放诞风流也。文群以身殉相如,相如亦以身殉文君,一琴一诔,已足千古也。
殉妇
《百妇谱》之
(谱壹拾捌)
清平乐。殉妇
家贫无福,人贱休谈禄。
敢问何方能享福,请到穹苍籁竺。
花妮绝食身亡,换来一栋牌坊。
牌坊庄中耸立,赚得爹爹官装。
第一回酒鬼丈夫烂醉渲淫,一通狂射精中带血
今生今世最爱酒,从早到晚不离手。
痛饮一樽豪情壮,连干二碗精神抖。
推杯换盏行酒令,拳来脚去狂斗殴。
稀里哗啦尿裤裆,翻江倒海喷出口。
花妮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会嫁给一个嗜酒如命丈夫,十里八村的乡邻们都称之为“酒鬼”。
新婚的那一天,披红戴花的新郎官陪客人饮酒,一桌酒席尚未陪完,客人尚未尽兴,酒鬼丈夫自己则醉倒了,被众人四脚朝天地抬进洞房里,咕咚一声扔在热滚滚的土炕上。
花妮从红盖头的下沿悄然望去,只见新郎官一动不动、仰面朝天的躺在土炕上,周身酒气升腾,很快便响起如雷的鼾声。
随着酒宴的继续进行,厨间的炉灶一刻不停地燃烧着,烟道与新房相连的土炕温度越烧越高,渐渐地新娘子嗅闻到一股呛人的腥骚闻,花妮大惊:“不好,夫君要烤糊喽!”新娘子等不及新郎官来揭盖头,自己掀到一旁,慌忙爬到酒鬼丈夫的身旁,一把揪住酒鬼的身子,急促地摇晃起来:
“快醒一醒,换个位置再睡,你的背脊都要烤焦了!”
酒鬼依然一动不动,仿佛死了一般,花妮只好用力推动着酒鬼,感觉新郎官虽然身躯庞大,体重却是极轻:这家伙,年纪轻轻,而身子则让烈性酒精给烧成一把柴炭了!花妮绝非危言耸听,大凡常年酗酒之人,其结局无不面黄肌瘦,体轻如柴,若果不加节制地继续酗酒,身体便慢慢地萎缩起来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佝偻症。
新娘子玉手稍一用力,便非常轻松地将酒鬼翻过身去,呼——登时,一股灼面的热气直扑花妮的面庞,新娘子顾不得因陌生而萌发的羞涩感,立刻给酒鬼丈夫宽衣去裤,烛光下,酒鬼丈夫的背脊因长时间受火炕的烤灼,呈着深沉沉的暗红色,如果不是花妮及早发现、及时改变体位,新婚之夜,烂醉的酒鬼新郎官没有做成,却被火炕烙成肉饼了。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花妮的手心突然触到一片骚咸咸的潮湿,定睛一瞧,好么,酒鬼丈夫好生有出息,居然喝得尿了裤裆:“夫君啊,”新娘子手拎着酒鬼丈夫湿漉漉、骚哄哄的裤子,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:“你再这样不知深浅地喝下去,纵然不喝死,也得喝成瘫子,待油枯灯尽之后,慢慢地死掉!”
新娘子的推断不是没有依据的,花妮的表哥也是远近闻名的大酒鬼,几年前开始尿失禁,今年三十岁方才出个小头,已经瘫痪在床了,身子日渐枯萎,用舅母的话说:他啊,待这点心血耗光之后,便万事大吉喽!
“渴啊,”给酒鬼去光了衣裤,压好被子了,花妮正待睡去,酒鬼突然嚷嚷起来:“渴啊,水,水啊,我要喝水啊!”
“来喽,来喽,”花妮急忙下炕,哗地舀起一瓢凉水递到酒鬼的面前,酒鬼瞪着红通通的醉眼,双手捧过大木瓢,咧开嘴巴,咕噜咕噜地、仿佛饮牛一般地狂灌起来。
“咳咳咳,咳咳咳,”也许是喝得太急了,也许是灌得太猛了,酒鬼突然剧烈地干咳起来,旋即推开水瓢,扑地吐出一口粘痰来:
“啊,渴死我了,渴得我嗓子好紧、好咸啊!”
“哎呀,”望着地上的痰泡,花妮惊呼起来:
“夫君,你已经喝出毛病了,痰中带血啊!”
“没关系,”新郎官抹了一把嘴唇上的水珠,不以为然地笑道:“没什么大不了的,老毛病了,酒喝多了就犯,把酒停下几天就好了!”说毕,酒鬼丈夫冲新娘子会心地淫笑一番,一把将花妮揽进被窝里。
花妮咯咯一笑:“瞅你瘦得骨包骨头,真没想到,还蛮有些气力呢!”
“嘿嘿,”酒鬼丈夫终于清醒了几分,笑嘻嘻地搂住新娘子:“亲爱的,我虽然表面看着又干又瘦的,可是,气力不逊他人,尤其是这方面,”说到此,酒鬼大大咧咧地将手掌探进花妮的胯间:“肥猪乃蠢货,瘦马配良种,我人瘦,可是本事大,亲爱的,你信不信?”
“呵呵,”花妮也顺势握住了酒鬼丈夫的小弟弟:“喝了这么多的酒,你还行么?”
“我,”酒鬼丈夫信心十足,“咚”的将花妮按在身下,挥枪翻到新娘子的身上:“你不知道,老子酒喝得越多电越足!”
虽然喝得抽筋扒骨,痰中带血,结婚之后,酒鬼丈夫非但没有把酒停下来几天,反倒变本加厉了,天天必饮,顿顿皆喝,每天早晨扒开眼睛便开始饮酒,新婚的花妮不便过份劝阻,只好委惋地求助于婆婆:“夫君的酒喝得太甚了,长此下去,会把身子喝坏的!”
“唉,”婆婆双手一摊,露出一副无奈之相。
“我的好媳妇啊,婆婆前世没做好事,积下这么个孽缘来,大概是我前世欠他些什么,生出这个么讨债鬼来,四岁那年,他姨妈娶儿媳妇,我抱着他去参加婚礼,酒席上,这七大姑八大姨的,你一口、他一口的逗他玩,左一口、右一口的耍弄他。结果啊,这一来二去的,就把我儿子给灌醉了,你猜怎么着?回到家里,我儿大哭大叫,满土炕的打滚,好不容易把他哄睡了。”
“第二天醒来,还要喝那马尿,我不给,他就哭,宁可不吃奶水,也要喝那马尿,唉,我没辙了,就弄来一瓶,兑上清水哄他,从此以后啊,就、就完喽,小小年龄就把大酒给练成了。我也板过他,不给他酒喝,可是不成啊,这小子一天没有酒喝,就好似大烟鬼没有大烟泡抽一样,馋得抓心挠肝,撕衣揪发,掀桌子砸碗,甚至,甚至……”
说到此,婆婆面呈难色:“媳妇啊,不怕你笑话,这个逆子啊,实在鳖得急了,就耍混了,甚至、甚至……在我的面前挥拳踹脚,活生生要打他亲娘啊。乖乖,媳妇啊,你说,这不前世积的孽怨么,我活生生地养了一个畜生啊,瞅那架式,我若再不让他喝,他的拳头当真就能落在我的脸上啊。他爹死得早,我一个妇道人家又降不住他,我又能怎么办呢?唉,”婆婆长叹一声:
“这个生疔玩意啊,他愿意怎么喝就怎么吧,我也不管了,我也管不了,我拿他算是彻底没辙了!”
“嗨——”听罢婆婆的讲述,花妮懊悔不迭,亦是一声长叹,心中暗暗嘀咕道:“父亲这是怎样给女儿相的亲啊!仅听媒婆一面之词,也不托人好生探访探访,便如此草率地将女儿嫁给一个酒鬼,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?”
既然已经练成酒鬼了,当然就具备职业喝手的水平了,大凡一个合格的酒鬼饮酒时,无需什么象样的佐酒菜:一条青瓜;十余颗五香花生米;半块豆腐便能喝光一海碗老白干,当寒冷的冬天来临时,万物萧疏,餐桌上的菜肴历历可数,而职业酒鬼全然不在乎这些,几块硬生生、凉哇哇的白菜帮子就可以心满意足地痛饮一场。
而花妮的酒鬼老公,有据可查的最佳纪录是:半个橘子喝掉了一斤二锅头!
俗话说: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!既然爹爹给自己选择了一个酒鬼夫君,花妮也只能认命了,不认命又能如何啊?这又能怪谁呢?要怪只能怪自己前世没做好事,今世生就了女儿之身!花妮虽然没有念过书,却也知道三纲五常,知道女人应该尊敬翁婆、伺候丈夫。
既然丈夫喜欢饮酒,家中再怎么清贫,也要尽可能地给夫君搞些佑酒的菜,以免身体继续这样地干枯下去:“老公,不能这样喝,”看见酒鬼嚼一口大葱,喝一大口酒,花妮心痛地劝阻道:“酒和葱都是生热的玩意,你这样热上加热,会把胃肠烧坏的,你先别喝了,等我把这只猪耳朵给你切了,再就着酒喝吧!”
酒鬼丈夫无菜佐酒时,喝得却也畅快,谁知贤慧的媳妇搞来了下酒菜,一大年也未曾闻生命,在下深表敬佩,”说到此,周郎中拱了拱双手,然后,以开导的口吻道:“老太太的精爷我,我,”柯老爷嗖地抽剑出鞘,恶狠狠地压在徐氏的脖子上:“砍掉你的脑袋,就仿佛杀只小鸡,而我上呈的材料中,只要写明你不安心工作,一切便结了,懂么?”
徐氏的哭声嘎然而止,柯老爷的话绝对不是吹牛,更非言过其实,不久前,总是倚在窗前观望的徐氏,亲眼看见柯老爷手刃了一个不安心做苦役的囚犯,真尤如杀了一只小鸡。徐氏确信,柯老爷说得出来,就能做得到,为了活下去,为了能够与爱人团圆,徐氏不得不止住了悲泣,将悲伤深深地埋进心田。看见徐氏不哭了,也不闹了,柯老爷呛啷一声宝剑入鞘,坐到徐氏的面前:“唉,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,他,他有什么让你如此依恋的,难道,我就得不到你的真情么?说,”柯老爷端着徐氏的下巴:“还想不想他了?”
“不想!”
“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小妾?”
“愿意!”
“哼,”柯老爷一把推开徐氏:“全是他妈的假话,敷衍人的假话,啊,”既然永远也得不到徐氏的真情,而徐氏的身体却是顺手拈来,只要一看见徐氏妖娆的身段,柯老爷便性致昂然,他一边松解着徐氏的裤带,一边由衷的感叹着:“你的心,我永远、永远也得不到了,只有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啊!”
于是,柯老爷搂着徐氏,在昏暗的烛光下,哼哼呀呀地折腾起来,徐氏则紧闭着双眼,很不情愿地迎接着柯老爷的冲击,娇艳的胴体随着飘眇的烛光,时尔忽上,时尔忽下,望着反射在墙壁上的折影,望着摇动的幔帐,柯老爷总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,在他的身后,仿佛有一个甩不掉,躲不开的阴影:他妈的,柯老爷确信,那阴影便是许三:你他妈的人是走了,阴魂却是不散啊,唉,看起来啊,你小子的阴影,将永远笼罩住老爷我的房间里,在我与徐氏之间,形成一道虽然看不见,却是厚重无比的隔断。
“老爷,”柯老爷正满腹心思地享受着徐氏的胴体,馆外突然嘈杂起来,有心腹的衙役急切地呼唤着柯老爷:“老爷,不好了,我们抓到一个剌客!”
“什么,”柯老爷大叫一声,咚地从徐氏身上跳了下来,慌忙披上睡衣,推门而出:“剌客,剌客在哪?”
“在这,”黑暗之中,巡夜的兵卒将一个汉子推到柯老爷面前:“就是他,不知何时潜入老爷的馆舍,鬼鬼祟祟地徘徊在老爷的窗下,我们观察他许久了,看见他居然蹬上了窗户,我们估摸着他大概要入室行剌了,就立刻动手,将其擒拿住,请老爷亲自过堂审讯他吧!”
“啊,”借着月光,柯老爷眨巴着昏花的老眼仔细一看,所谓的剌客,原来是自己白天才打发走的许三:“许三,原来是你,你,你他妈的不回老家去,到老爷的舍内想什么魂?”柯老爷心里比谁都清楚,许三想什么魂?当然是徐氏的魂啊!听了柯老爷的斥问,许三可怜兮兮地垂下头去,同时,掏出一只口袋,递向柯老爷,夜风袭来,袋里叮当作响,那是银子相撞发出的声响:“老爷,这银子,我不要了,我要我的老婆!”
“混蛋!”柯老爷大骂一声,盛怒之下,居然耍起了孩子脾气:“你想要,我偏偏不给,气死你,馋死你!左右,”
“在,”
“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打入牢内,明天我再收拾他!”
“是,”
左右将许三推下,许三依然苦苦地乞求着,柯老爷理也不理,忿然返回舍内,一夜无话。
第二清晨,柯老爷余怒未息,依然耍小孩子脾气,你许三不是想要老婆么?我非但偏偏不给,还要你天天能看得见她,让你看着自己的老婆是如何伺候我的,让你难堪,让你伤心,于是,柯老爷令左右打了许三一通板子,故意将其安排在舍内打杂,令徐氏不得走出寝室一步,否则,杀无赦,斩立绝。
每天早餐后,许三估计着柯老爷应该升堂审案去了,便停下手中的活计,痴呆呆地伫立在柯老爷馆舍的门前,双眼直勾勾地射向窗扇,而徐氏则撩起窗幔,依窗与汉子默默相望,彼此间用目光交谈着、倾述着。
心腹的衙役早就将这些情形反应给了柯老爷,与往常的情况不同的是,柯老爷并没有暴跳如雷,更没有破口大骂,闭堂之后,刷刷地写了一通请柬,然后差人发往各处:原来,柯老爷今天六十岁大寿,要请客欢宴。
清天大老爷六十寿诞,谁人不敢前来贺寿啊,酒席之上,推杯换盏之余,看见许三与众仆人端着盘子,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,柯老爷抿着嘴唇嘿嘿冷笑一声,冲左右使了一个眼色,心腹衙役立刻俯首帖耳到柯老爷耳畔:“老爷有何吩咐?”
“嘿嘿,去,”柯老爷一脸神秘地说道:“把徐氏唤来,老爷我要与她喝几杯!”
“是,”
左右得令退下,徐氏很快出现在酒席桌前,恰巧与许三撞个满怀,众人哗然,无不以异样的目光扫视着这对被柯老爷强行拆开的恩爱夫妻。柯老爷见状,啪的一拍桌子,徐氏慌忙躲开许三,而许三也知趣地托着空盘子,从徐氏的身旁溜出宴会厅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徐氏很不自然地走向柯老爷,柯老爷又是一番嘿嘿的冷笑,示意徐氏坐到自己的身旁。此时,许三又返回餐厅内,手中端着盛满菜肴的盘子,眼睛却牢牢地盯着柯老爷身旁的徐氏,柯老爷见状,一把揽过徐氏,就在众人面前,很是大方地啃吮着徐氏面红似火的脸蛋:“爱——卿,”但见柯老爷搂着徐氏,旁若无人地做出种种轻佻的举动,众人看在眼里,心里都清楚:柯老爷这是故意做给许三看的:“啊,”柯老爷甚至将手掌探进徐氏的酥胸里,肆意抚弄起来:“好肥实的大奶子啊,真是养手啊,令人越摸越爱摸啊,呵呵,”
“嗯,”徐氏无地自容地依在柯老爷的怀里,难为情地闭上眼睛。柯老爷一边摸着、一边啃着,一边问道:“爱不爱老爷啊!”
“爱!”
许三看在眼里,一颗心在淌血,端着盘子的双手,瑟瑟发抖,看见自己心爱的人,被他人肆意轻佻,许三恨不得挥起手中的盘子,无情地砸向情敌——柯老爷。柯老爷丝毫也不在乎,大大咧咧地端过一只酒杯,塞到徐氏的手上:“嘿嘿,既然爱我,就请喝一樽交杯酒吧,嘿嘿,”
“是,老爷,请,”徐氏接过酒杯,不待与老爷碰杯,脖子一仰,咕噜一声灌进嘴里,辣得小嘴直咧,呛得泪珠乱窜,趁着老爷仰脖干杯之际,徐氏突然闭开双眼,表情极为复杂地扫视着餐桌对面的许三。
“啊,好酒!”柯老爷放下空酒杯,吧嗒吧嗒厚嘴唇,一手搂着徐氏的粉颈,一手指着餐桌对面的许三:“实话告诉老爷,你还爱他么?”
“这,”徐氏哑然,不知如何作答:“这,这,”徐氏吱唔了半晌,突然扬起面庞,壮着胆量,真诚地说道:“爱——!”
“哇——,”徐氏此言即出,举座皆惊,大家的目光纷纷转向柯老爷,不知难堪之下的官老爷如何收拾这个始终不回心转念的小妾。柯老爷放下酒杯,扫视一番四周,又咄咄地逼视着许三,而徐氏突然胆怯起来:“老爷,我说错了,我,我,”
“不,”柯老爷缓缓地站起身来:“你没说错,你说的是真心话,唉,”柯老爷已经有几分醉意了,又经徐氏这番嘲弄,渐渐有所顿悟,只听醉汉结结巴巴地言道:“古人云:宁拆一座坟,不拆一个婚,强拧的瓜不甜,既然徐氏的心里始终装着自己的原配丈夫,我从中作的什么梗啊,”
“老爷言之有理,”众人皆赞:“老爷不愧是京城来的大官,听了老爷这番话,在下胜读十年书啊!”
“所以,”众人的奉承,听得柯老爷飘飘然了:“左右,”
“在,”
“备马,送许三、徐氏回老家!”
“老爷,这,”左右茫然了:“老爷此话当真?”
“谁跟你们开玩笑呢?”
“谢谢老爷!”
徐氏扑通一声跪倒在柯老爷的脚下,许三见状,将托盘放在餐桌上,绕过餐桌,来到柯老爷面前,也一脸感激地跪了下来:“谢谢老爷!”
“唉,”柯老爷摆了摆手,说出来的一句话,把大家都逗乐了:“趁着本老爷尚未清醒之前,你们小两口还不快快离开此地,回家好生过日子去!”
「妇谱氏曰」
一个弱女子,因丈夫获罪而受牵连,在遥远的边关服苦役,不仅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,且不攀附权贵,不阿谀官僚,更不嫌弃窝囊的丈夫,虽然委身于官老爷,心中仍旧思念着结发的丈夫,其忠贞之心诚可叹也。现实生活中,莫说丈夫因罪入狱,往往因丈夫没有本事,赚不到钱,老婆便一拍屁股走人喽!
贵妇
《百妇谱》之()
《百妇谱》之
贵妇
(谱玖)
钗头凤•我爱表姐。
红脸蛋,白细手,婀娜妖身似杨柳。
春风绿,芳姿绰,心中挚爱,嘴上乞索。
摸,摸,摸!
空思念,为人妇,家境寒,貌奇丑,白天鹅,粪池落。
故人已去,旧情难却。
愕,愕,愕!
第一回调皮鬼想当小女婿,大美人不做唐惠仙
我家表姐初长成,面容姣好体轻盈。
提前一载登金榜,才貌双全满楼倾。
我的大表姐——毛毛,生得特别漂亮,真的,我今天没喝,头脑很清醒。大表姐的漂亮绝对不是我自己吹嘘出来,那是整个宿舍楼里公认的。当我还是一个抹着大鼻涕、满宿舍楼里调皮捣蛋的混噩顽童时,毛毛大姐已经出落成一个身材高佻、肌白肤嫩的婀娜小美人了。她就读于很是著名的省实验中学,每天放学时,走进宿舍楼的大院子,看见满脸灰土、浑身泥浆的我,大表姐不禁秀皱紧锁,厥着小嘴喋喋不休地训斥着我:“你瞅你弄得,哪里还有点人样啊,走,跟姐姐回家去,姐姐给你洗一洗!”
表姐一边嘟哝着,一边伸过细白的小手,模仿着舅妈的神态,像个小大人似地拧着我的耳朵。望着表姐那苗条的腰身,扭来扭去的丰臀,我一边佯装痛疼地、哎哟哎哟地尖叫着,一边高高地举起手中的黄泥,狠狠地抛掷在水泥地板上,只听叭的一声脆响,黄泥炮遍地开花,星星点点的泥浆溅在毛毛姐曲线优美、起伏不平的胸脯上,吓得她立刻松开细手,妈呀一声怪叫,连拍打身上的泥浆都顾不得,便连蹦带跳地落荒而逃了。
俏丽的大表姐是我的骄傲,而捉弄娇里娇气、柔声细语的小美人,也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摔够了泥泡,玩腻了玻璃球,我又逮住一只无家可归,在走廊的暖气沟里栖身的流浪猫仔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