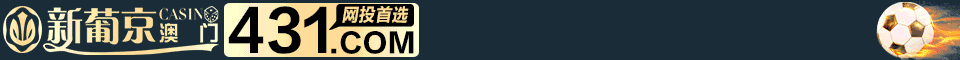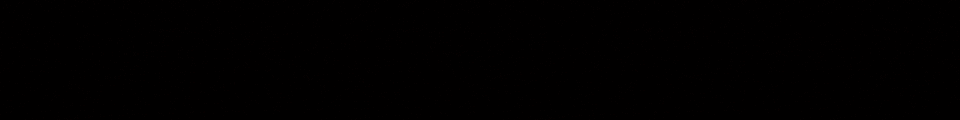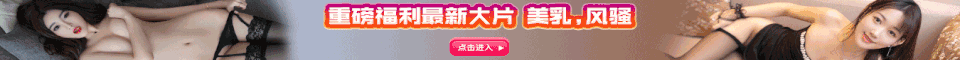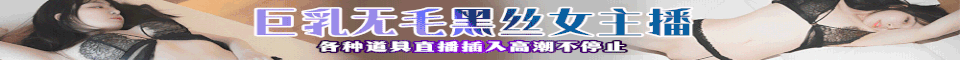我是一名乡村教师
一宿暴雨,雷鸣夹着闪电,似乎要把整个小屋震得粉碎,摔个稀烂……我第一次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力,是种震颤又无处可逃的惊慌。24年来,我的确是第一次听见这么霹雳的雷声,看见这样狂抽着的闪电。暴雨哗哗哗地仍下个不停。
无法安眠的夜晚。我伸手去拧桌上的台灯,不亮,大概已经停电好一会了。
我只能继续发愣听雨声,看闪电鞭打小屋,感受一股股涌上来的震颤和惊悸。
到宜山已经2个多礼拜了,并不象之前想的那么糟糕。相反,这里景色清丽,山秀水美,乡民待人热情;工作上课程也不繁重,孩子们都挺讨人喜爱,同事间相处友好。似乎找不到不满足的地方了,但我心里还是觉得别扭,仍然被一种遗弃感笼罩着。
2001年我从川大在自贡的一个分校毕业,算是拿了个计算机专业的大专文凭。随后飘到成都,又飘到过重庆,也在附近一些小城市待过,都是不好找工作。我还想到更远的地方试试,却就在刚要动身的那几天,接到家里人带过来消息,说人事局今年呀招考一批公办教师。两个条件,一是本市户口,全日制大专文凭,毕业三年内还未谋到工作;二是录取后得到山区支教二年,回去再正式分配到条件较好的城镇学校任教。乖乖,冲着老家那个省会城市的公办教师指标,我也完全值得去考,在山区支教2年,也完全是可以忍受的。
就这么着,我幸运地考取并被分派到了贵州省遵义附近的一个小镇小学来。
一切才刚开始,忍受吧。
就在我入神回忆并自怜叹息时,听见一阵焦急用力的拍门声。我支起身子,凝神听了下,的确是有人拍门。是谁呢,这么晚了?虽然没看表,但估计怎么着也该十点过了吧。我有些狐疑,一时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去开门。
拍门声更急了!惨白的电光,一个接一个的滚雷,加上这急迫的敲门声,我感到了一丝恐惧。这时才听到门外在喊:「陈力!陈力!」一听声音我才缓了口气,是隔壁杨姐。说隔壁其实也不算。学校里只有一排住宿房,共四家人。我被分在房档头这间,原来是校广播室,现在也是,只不过拉了道布帘子,里间成了我的卧室兼办公用。我的隔壁是保管室,再过去才是杨姐家。她和另外两家各占两个房间,算是卧室和厨房。
听她语气急迫,我忙披上衣服。开门那刻正好赶上一轮哧啦啦吐着信子的闪电,杨姐穿件雨衣,几绺飘出来的头发正滴着雨水,一脸的着急。
「怎么了,杨姐?」
「哎呀,气死了!你王哥又不在家,张老师也喊不答应,我又不好去喊巫主任。我家后院的鸡笼子垮了,鸡飞得到处都是……」听她这么一梭子子弹般干脆的话,我才知道是来喊我帮她把鸡先逮进屋去。
说完她就递过来一件雨衣,也不待我同意。杨姐就这么个爽快人,虽然才来不久,几个照面下来我就能感受得到。
他们几家都在房子后面圈了个院子出来,种点蔬菜,养养鸡什么的。一时,杨姐和我就在雷雨闪电中东追西拦,感觉也太滑稽了。院子虽小,但因为夜黑和泥泞,着实捉了一会才算逮齐了这九只鸡。
杨姐抱歉地说着让你弄一身泥的话,过会端了盆热水过来。趁闪电一瞬后,我估摸着去接,不想手伸过去正摸到一个鼓囊着的柔软圆滑的东西,我吃了一惊,慌忙缩手,而杨姐也是不意料的小小一惊,却把要喊出的惊讶掐灭在喉咙里。
都知道是因为夜黑。
「今天太麻烦你了,谢谢哈!」在不小心亲密接触了一下后,似乎才提醒了我俩是身在一个漆黑夜里的同一间屋子,杨姐说着就回去了。
我擦洗过后,躺在床上,却再没有了去回忆大学憧憬未来的心情,满脑子的那比闪电更短暂的一触:她的乳房好柔软,似乎又很有弹性;无名指感受到的那粒突起,是不是乳头,突得好厉害;为什么那么一触就缩手的瞬间,居然能摸得这么清楚,难道没戴乳罩;为什么今天我感受这么强烈……好一会我都陷在对刚才那风华绝代「一触」的回味中,下面小弟弟早已硬得不象话了。
说实话我虽然相貌平平,但总算是在大学里也还谈过几次所谓的恋爱,都是上了床,也自认为是个曾深入地体验过女人肉体的男人。可这次为什么这样了呢?我不知道,闭着眼睛,想着杨姐的模样,用手开始套弄起小弟弟来。
经常会听见有人这么评价女人:长得绝对算不上漂亮,但很耐看。杨姐就有点属于这种女人。以前,我一直搞不懂既然不漂亮了为什么还有耐看一说,现在仔细想像她平日举手投足、撩发微笑、凝目顾盼等等细微处的神采,应该归为一种叫风韵的东西吧。而至于风韵又是什么,就实在再说不出来。何况,才短短几分钟,我感觉小弟弟已经再也憋不住了——噢!一股浓液喷洒出来,正应着一声霹雳惊雷……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精液的气味,我喘着气,微翕的嘴里小声地也是宣誓般地念着「杨静秋,我要你!要你!」杨静秋就是杨姐,学校总务处主任,30来往岁。我刚来时就是她负责接待安排住宿,初印象是说话干脆办事也利落,才几句话下来就以姐弟相称。我不知道这是山区人民的直爽,还是她处事的方式。因为是隔壁,我又初来,所以她常以姐姐或叫领导身份过来看看,于生活上也多有照顾。她老公我叫王哥的在县里上班,好像是给哪个公司老板开私车,不定时回来,也是个容易交往的人,爱和他在一起喝点小酒、聊天、互相散烟。
暴雨夜和杨姐天外飞鸿般一触后,在接下来的日子,我就特别期待和她接近了。她不见有什么异样,还是很平常的问吃了没有啊,端菜过去凑份子啊,傍晚喊一起逛路什么的。每天我都享受着这些琐碎的欢乐,并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习惯了夜里用手去想她,每次,都很热烈。在那短暂的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里,她的说话、手指、指上那枚戒指、淡淡的体味在脑中一次次地具体起来,又在那喷射的刹那全部模糊、远去……我这是怎么了?爱上她了么?绝不可能!别说她有家室,有个十岁的孩子;也别说我只待两年就回城里,有稳定的工作;就她30多岁的年龄,山区环境造成的生活意识,甚至心直口快的性格,都不会让我爱上她。
那时我还不知道其实世间真的有寂寞一词,而并不是只在歌里唱唱。也许你还常常在人堆中发自内心的欢喜愉悦,但你的灵魂无所慰藉和倚靠,你的心灵是一匹草原上奔腾或流浪的马,你的家园只是栅栏后一个空荡荡的房间。我那时就应该是寂寞着,只是被青春的贪玩和猎奇的欲望所支配,而没有体察到,也不想去思考罢了。
转眼半个学期过去,半期考试后我去给赵校长请假,想回家一趟。已近退休的赵校长听我说完后,沉吟了下说:「哦,是这样。我还打算说让你趁这几天到县城给学校买点易耗品呢。既然这样,那……」听赵校长这么一说,我联想到自己刚来,最该搞好和校长的关系,赶紧抢过话头,「既然有事那我就等暑假再回家吧!本来假期也才三天,只够把时间花在路上。」赵校长抬头看看我,笑了。
「也是,年轻人,才待二个月就想家喽,哈哈哈,是得在这里锻炼锻炼。」我花了两天从县城买了一大堆东西,顺便逛了逛这个古城,权当公费游览民俗小镇。回校后,还赶着要到杨姐那里报帐、入库、签字。但她没在,可能假期到老公那里去了,等到次日下午才看见她一个人回来。晚饭后杨姐和我到办公室办理这些,不知不觉忙完时已是夜色很浓了。她打个呵欠,说着好累。我们刚要离开办公室回去,突然四周一片漆黑。「又停电了!」小镇上停电真的是很频繁的。杨姐倒是平静着说:「呵呵,习惯了就好。」眼睛一时还不能适应这陡然来的黑暗,我和她摸摸索索地朝前走,她说着「把灯关上,免得费电」时大概站在门口摸开关,我走上来正好撞进她怀里。「呃——」她小声的惊呼,正是这熟悉的一声惊呼,在我脑里电弧一样勾起一个多月前那一触乳的风情,又极速联想起许多天来对她的渴望,霎时,我再也不能忍住自己的欲望,将错就错,一把搂定她的身体。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,让杨姐吃惊不小,等我的双手猛地环住她腰部的时候,她可能才确定这次不再是误撞。她第一反应是迅速用手抵住我的胸口,「陈力,你干什么,快放手!」,话里有几分慌乱。我从她压抑着的音量里获取了胆量,手下用力,把她带回屋子朝里那方,又把她推靠到墙边并用下身抵紧控制她的身体。在一个24岁的男人面前,她所谓的抵抗其实完全可以忽略不计,其实也只是揪着我衣领可笑地想把扯开和重断重复低吼的一句「别这样,陈力!陈力,别这样!」我用嘴在她扭动不安的颈项处搜索,同时腾出只手用力抚摸她的腰和臀间。
说实话,她挣扎的是比较厉害的,也许是力气也不算小。我虽然没有强迫的经验,也知道这不是一场能迅速取得胜利的征战。在一番索取中,我的小弟弟已经硬得不行了,恶作剧地不断扎向她腿间,虽然隔着裤子,仍能感受到每次她都颤抖着,仿佛是要一点点瓦解她的反抗。我把嘴移动到她耳边,急促而恳切地说:「杨姐,我想你,给我,给我!」。又一轮手的搜索,「给我,杨姐,你不知道我每天都想你,想要你!」事后总结,这实在是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能撼动女人的话——既表达了对她的渴望,尤其是身体的渴望(也就侧面说明她的身体对男人具有吸引力,满足了女人如月经般无一例外的虚荣心),又不至流于市井间赤裸裸的日、干、插、弄、操等的粗俗和龌龊。佩服中国传统文化一个——「要」这个字在这里,在这种情况下,是何等及时关键,能化兽欲于文雅啊!
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,是因为杨姐正是在这几句火线宣言的表达后放弃了她的负隅反抗。她的手静止在我的衣领,我也中止了粗暴,化情欲于温柔,开始一点点、一寸寸、一层层细致地挑弄。
先是从她腰部开始,按摩似的抚摸。手逐渐蛇行移动到肚皮上,发现有点赘肉,但正好增强了肉感。又把手徐徐覆盖(发现覆盖不住)在乳罩上,不是那种不尊敬的如日本人似的大力揉捏,而是轻风拂过似的抚弄——兄弟们,此刻我惊喜地发现,她的呼吸乱了。再把手迂回绕到她后背,也是肉感十足,但嫩而光滑。「嗒——」那一刻,我甚至听到了乳罩扣子和扣眼相互解脱的声音——是当时屋子里太静,还是我太敏感形成幻听?时至今日,这一声「嗒——」仍是我疲倦时促生性欲的有效想像之一。
「嗒——」一响中,伴随着她一次深呼吸,我知道,她允许了我。两碗释放后的乳肉在手中温柔地流淌,一张湿润的嘴在她颈项和双乳间如邮递员般繁忙,传递着彼此越来越兴奋的证据。
她的乳头硬了,不知是哺乳过还是经常抚摸的原因,有樱桃果儿般大小。每次用舌去舔,就加强了她的呼吸。
书上说,三十如狼,四十如虎。在杨姐生命中的狼虎之间,我不想也不敢让她失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渐次刺激后,她小声地说:「会有人来的。」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催促我实质性进入的话语。我默不作声,把手从牛仔裤探入她双腿间。那里,湿得厉害。在手指触到阴部的时候,她甚至是低唤了一声。我不知道这一声和之前的惊叫的区别,也不愿意再多想,就把她逐件剥去,放倒在桌子上。
我更像一个耐心的猎人,把其实已经硬如生铁的小弟弟,在她阴部上擦来抹去,既象要预湿,又像挑逗。杨姐果然耐不住,欠起身子扶住我肩膀,说:「来!」在习惯了黑暗的夜色中,我把小弟弟捅入杨静秋的下体。「唔……」该怎么来形容那一进入的美妙呢,我想只能以这一声沉闷着的浅哼表达。舒服,她下体的嫩肉包裹着我的阴茎,湿而滑,每次抽插都毫不费力。
关于做爱中的呻吟,请别笑我的无知。我以前只以为A片中的叫声是配合影片的需要,因为和我共枕过的几位学友都只是痛苦着承受。那时我知道了,世间还真有因快乐而痛苦般呻吟一说。杨姐那刻就是这样:月晕的微光中,她微翕的嘴里,伴随着我插入的节奏和力度,发出时紧时缓,小小的,微弱音量的呻吟;脸上闭着眼,尽是无助的表情;双手如同盲人般找寻我的肩膀……事后我曾几次问过她,她被问急了,说:「你以为我想叫啊?」当时我就惊诧着,逐渐用力起来,办公室里响彻着肉与肉碰撞的声音,是「啪啪啪」的。她起初随意放置的手,也渐渐扣住桌沿,有渐渐扶住我的手臂,再渐渐僵直地在空中如伟人辞别般挥舞,我知道,她愉快着,至少是她的身体愉快着。
在一阵盲目但有规律的猛冲后,我感受着她双腿和双手的同时用力,一股肯定是浓重的精液尽数喷射到她身体深处。「哗——」像闪电后天空的暂时宁静,我粗重的喘息,她小小的颤抖。下面,紧紧包裹着我小弟弟的空间在节律性痉挛,她的双手从我肩膀上一寸寸划落。
「啊——」仿佛是过了几个世纪,她的一声无所顾忌的叹息,让我把汗水中的头从她颈窝处探出来。
她没有继续说出什么,我也迅速抽出小弟弟。简单清理后,我和她分别消失于浓重暗夜中不同的房间门口。
那是2003年5月的某日,我回去后,居然再次习惯性的爱抚了小弟弟一次,因为,太强烈了!
【完】
无法安眠的夜晚。我伸手去拧桌上的台灯,不亮,大概已经停电好一会了。
我只能继续发愣听雨声,看闪电鞭打小屋,感受一股股涌上来的震颤和惊悸。
到宜山已经2个多礼拜了,并不象之前想的那么糟糕。相反,这里景色清丽,山秀水美,乡民待人热情;工作上课程也不繁重,孩子们都挺讨人喜爱,同事间相处友好。似乎找不到不满足的地方了,但我心里还是觉得别扭,仍然被一种遗弃感笼罩着。
2001年我从川大在自贡的一个分校毕业,算是拿了个计算机专业的大专文凭。随后飘到成都,又飘到过重庆,也在附近一些小城市待过,都是不好找工作。我还想到更远的地方试试,却就在刚要动身的那几天,接到家里人带过来消息,说人事局今年呀招考一批公办教师。两个条件,一是本市户口,全日制大专文凭,毕业三年内还未谋到工作;二是录取后得到山区支教二年,回去再正式分配到条件较好的城镇学校任教。乖乖,冲着老家那个省会城市的公办教师指标,我也完全值得去考,在山区支教2年,也完全是可以忍受的。
就这么着,我幸运地考取并被分派到了贵州省遵义附近的一个小镇小学来。
一切才刚开始,忍受吧。
就在我入神回忆并自怜叹息时,听见一阵焦急用力的拍门声。我支起身子,凝神听了下,的确是有人拍门。是谁呢,这么晚了?虽然没看表,但估计怎么着也该十点过了吧。我有些狐疑,一时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去开门。
拍门声更急了!惨白的电光,一个接一个的滚雷,加上这急迫的敲门声,我感到了一丝恐惧。这时才听到门外在喊:「陈力!陈力!」一听声音我才缓了口气,是隔壁杨姐。说隔壁其实也不算。学校里只有一排住宿房,共四家人。我被分在房档头这间,原来是校广播室,现在也是,只不过拉了道布帘子,里间成了我的卧室兼办公用。我的隔壁是保管室,再过去才是杨姐家。她和另外两家各占两个房间,算是卧室和厨房。
听她语气急迫,我忙披上衣服。开门那刻正好赶上一轮哧啦啦吐着信子的闪电,杨姐穿件雨衣,几绺飘出来的头发正滴着雨水,一脸的着急。
「怎么了,杨姐?」
「哎呀,气死了!你王哥又不在家,张老师也喊不答应,我又不好去喊巫主任。我家后院的鸡笼子垮了,鸡飞得到处都是……」听她这么一梭子子弹般干脆的话,我才知道是来喊我帮她把鸡先逮进屋去。
说完她就递过来一件雨衣,也不待我同意。杨姐就这么个爽快人,虽然才来不久,几个照面下来我就能感受得到。
他们几家都在房子后面圈了个院子出来,种点蔬菜,养养鸡什么的。一时,杨姐和我就在雷雨闪电中东追西拦,感觉也太滑稽了。院子虽小,但因为夜黑和泥泞,着实捉了一会才算逮齐了这九只鸡。
杨姐抱歉地说着让你弄一身泥的话,过会端了盆热水过来。趁闪电一瞬后,我估摸着去接,不想手伸过去正摸到一个鼓囊着的柔软圆滑的东西,我吃了一惊,慌忙缩手,而杨姐也是不意料的小小一惊,却把要喊出的惊讶掐灭在喉咙里。
都知道是因为夜黑。
「今天太麻烦你了,谢谢哈!」在不小心亲密接触了一下后,似乎才提醒了我俩是身在一个漆黑夜里的同一间屋子,杨姐说着就回去了。
我擦洗过后,躺在床上,却再没有了去回忆大学憧憬未来的心情,满脑子的那比闪电更短暂的一触:她的乳房好柔软,似乎又很有弹性;无名指感受到的那粒突起,是不是乳头,突得好厉害;为什么那么一触就缩手的瞬间,居然能摸得这么清楚,难道没戴乳罩;为什么今天我感受这么强烈……好一会我都陷在对刚才那风华绝代「一触」的回味中,下面小弟弟早已硬得不象话了。
说实话我虽然相貌平平,但总算是在大学里也还谈过几次所谓的恋爱,都是上了床,也自认为是个曾深入地体验过女人肉体的男人。可这次为什么这样了呢?我不知道,闭着眼睛,想着杨姐的模样,用手开始套弄起小弟弟来。
经常会听见有人这么评价女人:长得绝对算不上漂亮,但很耐看。杨姐就有点属于这种女人。以前,我一直搞不懂既然不漂亮了为什么还有耐看一说,现在仔细想像她平日举手投足、撩发微笑、凝目顾盼等等细微处的神采,应该归为一种叫风韵的东西吧。而至于风韵又是什么,就实在再说不出来。何况,才短短几分钟,我感觉小弟弟已经再也憋不住了——噢!一股浓液喷洒出来,正应着一声霹雳惊雷……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精液的气味,我喘着气,微翕的嘴里小声地也是宣誓般地念着「杨静秋,我要你!要你!」杨静秋就是杨姐,学校总务处主任,30来往岁。我刚来时就是她负责接待安排住宿,初印象是说话干脆办事也利落,才几句话下来就以姐弟相称。我不知道这是山区人民的直爽,还是她处事的方式。因为是隔壁,我又初来,所以她常以姐姐或叫领导身份过来看看,于生活上也多有照顾。她老公我叫王哥的在县里上班,好像是给哪个公司老板开私车,不定时回来,也是个容易交往的人,爱和他在一起喝点小酒、聊天、互相散烟。
暴雨夜和杨姐天外飞鸿般一触后,在接下来的日子,我就特别期待和她接近了。她不见有什么异样,还是很平常的问吃了没有啊,端菜过去凑份子啊,傍晚喊一起逛路什么的。每天我都享受着这些琐碎的欢乐,并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习惯了夜里用手去想她,每次,都很热烈。在那短暂的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里,她的说话、手指、指上那枚戒指、淡淡的体味在脑中一次次地具体起来,又在那喷射的刹那全部模糊、远去……我这是怎么了?爱上她了么?绝不可能!别说她有家室,有个十岁的孩子;也别说我只待两年就回城里,有稳定的工作;就她30多岁的年龄,山区环境造成的生活意识,甚至心直口快的性格,都不会让我爱上她。
那时我还不知道其实世间真的有寂寞一词,而并不是只在歌里唱唱。也许你还常常在人堆中发自内心的欢喜愉悦,但你的灵魂无所慰藉和倚靠,你的心灵是一匹草原上奔腾或流浪的马,你的家园只是栅栏后一个空荡荡的房间。我那时就应该是寂寞着,只是被青春的贪玩和猎奇的欲望所支配,而没有体察到,也不想去思考罢了。
转眼半个学期过去,半期考试后我去给赵校长请假,想回家一趟。已近退休的赵校长听我说完后,沉吟了下说:「哦,是这样。我还打算说让你趁这几天到县城给学校买点易耗品呢。既然这样,那……」听赵校长这么一说,我联想到自己刚来,最该搞好和校长的关系,赶紧抢过话头,「既然有事那我就等暑假再回家吧!本来假期也才三天,只够把时间花在路上。」赵校长抬头看看我,笑了。
「也是,年轻人,才待二个月就想家喽,哈哈哈,是得在这里锻炼锻炼。」我花了两天从县城买了一大堆东西,顺便逛了逛这个古城,权当公费游览民俗小镇。回校后,还赶着要到杨姐那里报帐、入库、签字。但她没在,可能假期到老公那里去了,等到次日下午才看见她一个人回来。晚饭后杨姐和我到办公室办理这些,不知不觉忙完时已是夜色很浓了。她打个呵欠,说着好累。我们刚要离开办公室回去,突然四周一片漆黑。「又停电了!」小镇上停电真的是很频繁的。杨姐倒是平静着说:「呵呵,习惯了就好。」眼睛一时还不能适应这陡然来的黑暗,我和她摸摸索索地朝前走,她说着「把灯关上,免得费电」时大概站在门口摸开关,我走上来正好撞进她怀里。「呃——」她小声的惊呼,正是这熟悉的一声惊呼,在我脑里电弧一样勾起一个多月前那一触乳的风情,又极速联想起许多天来对她的渴望,霎时,我再也不能忍住自己的欲望,将错就错,一把搂定她的身体。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,让杨姐吃惊不小,等我的双手猛地环住她腰部的时候,她可能才确定这次不再是误撞。她第一反应是迅速用手抵住我的胸口,「陈力,你干什么,快放手!」,话里有几分慌乱。我从她压抑着的音量里获取了胆量,手下用力,把她带回屋子朝里那方,又把她推靠到墙边并用下身抵紧控制她的身体。在一个24岁的男人面前,她所谓的抵抗其实完全可以忽略不计,其实也只是揪着我衣领可笑地想把扯开和重断重复低吼的一句「别这样,陈力!陈力,别这样!」我用嘴在她扭动不安的颈项处搜索,同时腾出只手用力抚摸她的腰和臀间。
说实话,她挣扎的是比较厉害的,也许是力气也不算小。我虽然没有强迫的经验,也知道这不是一场能迅速取得胜利的征战。在一番索取中,我的小弟弟已经硬得不行了,恶作剧地不断扎向她腿间,虽然隔着裤子,仍能感受到每次她都颤抖着,仿佛是要一点点瓦解她的反抗。我把嘴移动到她耳边,急促而恳切地说:「杨姐,我想你,给我,给我!」。又一轮手的搜索,「给我,杨姐,你不知道我每天都想你,想要你!」事后总结,这实在是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能撼动女人的话——既表达了对她的渴望,尤其是身体的渴望(也就侧面说明她的身体对男人具有吸引力,满足了女人如月经般无一例外的虚荣心),又不至流于市井间赤裸裸的日、干、插、弄、操等的粗俗和龌龊。佩服中国传统文化一个——「要」这个字在这里,在这种情况下,是何等及时关键,能化兽欲于文雅啊!
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,是因为杨姐正是在这几句火线宣言的表达后放弃了她的负隅反抗。她的手静止在我的衣领,我也中止了粗暴,化情欲于温柔,开始一点点、一寸寸、一层层细致地挑弄。
先是从她腰部开始,按摩似的抚摸。手逐渐蛇行移动到肚皮上,发现有点赘肉,但正好增强了肉感。又把手徐徐覆盖(发现覆盖不住)在乳罩上,不是那种不尊敬的如日本人似的大力揉捏,而是轻风拂过似的抚弄——兄弟们,此刻我惊喜地发现,她的呼吸乱了。再把手迂回绕到她后背,也是肉感十足,但嫩而光滑。「嗒——」那一刻,我甚至听到了乳罩扣子和扣眼相互解脱的声音——是当时屋子里太静,还是我太敏感形成幻听?时至今日,这一声「嗒——」仍是我疲倦时促生性欲的有效想像之一。
「嗒——」一响中,伴随着她一次深呼吸,我知道,她允许了我。两碗释放后的乳肉在手中温柔地流淌,一张湿润的嘴在她颈项和双乳间如邮递员般繁忙,传递着彼此越来越兴奋的证据。
她的乳头硬了,不知是哺乳过还是经常抚摸的原因,有樱桃果儿般大小。每次用舌去舔,就加强了她的呼吸。
书上说,三十如狼,四十如虎。在杨姐生命中的狼虎之间,我不想也不敢让她失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渐次刺激后,她小声地说:「会有人来的。」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催促我实质性进入的话语。我默不作声,把手从牛仔裤探入她双腿间。那里,湿得厉害。在手指触到阴部的时候,她甚至是低唤了一声。我不知道这一声和之前的惊叫的区别,也不愿意再多想,就把她逐件剥去,放倒在桌子上。
我更像一个耐心的猎人,把其实已经硬如生铁的小弟弟,在她阴部上擦来抹去,既象要预湿,又像挑逗。杨姐果然耐不住,欠起身子扶住我肩膀,说:「来!」在习惯了黑暗的夜色中,我把小弟弟捅入杨静秋的下体。「唔……」该怎么来形容那一进入的美妙呢,我想只能以这一声沉闷着的浅哼表达。舒服,她下体的嫩肉包裹着我的阴茎,湿而滑,每次抽插都毫不费力。
关于做爱中的呻吟,请别笑我的无知。我以前只以为A片中的叫声是配合影片的需要,因为和我共枕过的几位学友都只是痛苦着承受。那时我知道了,世间还真有因快乐而痛苦般呻吟一说。杨姐那刻就是这样:月晕的微光中,她微翕的嘴里,伴随着我插入的节奏和力度,发出时紧时缓,小小的,微弱音量的呻吟;脸上闭着眼,尽是无助的表情;双手如同盲人般找寻我的肩膀……事后我曾几次问过她,她被问急了,说:「你以为我想叫啊?」当时我就惊诧着,逐渐用力起来,办公室里响彻着肉与肉碰撞的声音,是「啪啪啪」的。她起初随意放置的手,也渐渐扣住桌沿,有渐渐扶住我的手臂,再渐渐僵直地在空中如伟人辞别般挥舞,我知道,她愉快着,至少是她的身体愉快着。
在一阵盲目但有规律的猛冲后,我感受着她双腿和双手的同时用力,一股肯定是浓重的精液尽数喷射到她身体深处。「哗——」像闪电后天空的暂时宁静,我粗重的喘息,她小小的颤抖。下面,紧紧包裹着我小弟弟的空间在节律性痉挛,她的双手从我肩膀上一寸寸划落。
「啊——」仿佛是过了几个世纪,她的一声无所顾忌的叹息,让我把汗水中的头从她颈窝处探出来。
她没有继续说出什么,我也迅速抽出小弟弟。简单清理后,我和她分别消失于浓重暗夜中不同的房间门口。
那是2003年5月的某日,我回去后,居然再次习惯性的爱抚了小弟弟一次,因为,太强烈了!
【完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