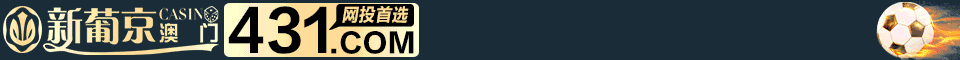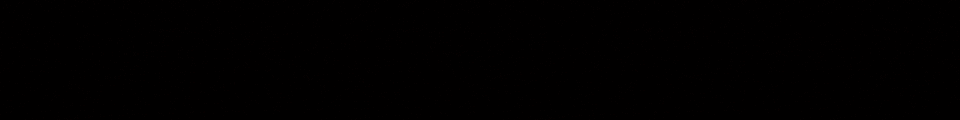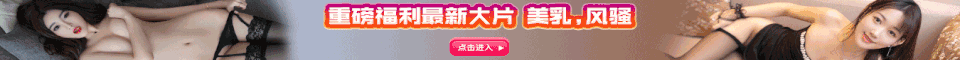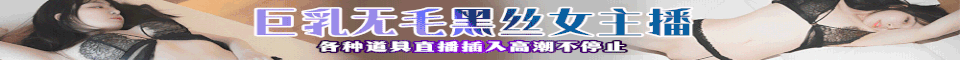苦中做乐
悲慘人生
北国,隆冬,大雪纷飞。
如果過的是和自己身分不相稱的生活,我就會時時感覺自己站的地方是傾斜的,於是經常要努力調整姿勢,擺一個和傾斜的地面相應的角度,如此才能保持站立的姿態……我的焦慮往往準時萌生。不管在什麼地方,不管正在做什麼事,天黑一到,就立即感覺到一股悶悶的,很難形容的焦慮的痛覺發自胃的底部,一點一點爬上來,向左滲透,向右擴散,終至感覺到整個胃又硬又重,像一塊巨石般盤踞在身體的正中央。晚上,焦慮中丈夫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,整夜整夜的咳,吃过药反而更加激烈。屋子里,我不敢生炉子,害怕烟气呛著他,生病的女儿因为寒冷,只是蜷缩在床脚瑟瑟发抖,我问她什么都不说。临家的奶奶心眼好,大早晨就送来一壶开水,我忙活著为丈夫倒水,多少能帮他暖和一点。
清晨,当一缕阳光从房间里破旧的窗户照射进来的时候,丈夫的咳嗽突然停了下来,他喘息著对我说:「老婆,给孩子弄点吃的吧,别饿著她。」说完,丈夫躺下去,闭上眼睛。我点点头,穿上棉衣走出门去。门一打开,外面的雪花就吹了进来,我赶忙走出去把门关好。啊!天气真冷啊!天地彷彿被冻得凝固,到处是一片白色。胡同里也逐渐开始有了声气,家家户户开始了一天的忙碌,烟囱里冒出阵阵的轻烟,配合著这浑然的白色,别有一番景象。
在胡同口就有叫卖的小摊,油条、豆浆、小米粥、豆包……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。
我虛弱的一步一步走到胡同口,小摊前面稀稀拉拉的有几个买早点的人。
「一碗小豆粥,两个豆包,两根油条。」我掏出一块五角钱递过去。
「两元!油涨 了。」满身油渍的老闆说。
我犹豫了一下,又再掏出五毛钱给他。
他抬头看看我,然后把东西包好,递到我的手里,对我说:「你慢点走,道路滑。」
我没说什么,捧著东西一步步走回家去。
回家以后,急忙把东西分开,小豆粥、豆包、油条都分成两份,生病的女儿闻到了香气也摸著床槓爬了过来,丈夫又开始咳嗽起来。我走过去,帮著他坐在床上,一边拍著他的后背,一边说:「吃点东西吧?唉,怎么这么咳呢?」
丈夫说:「呵呵……别吃那药了,吃了也没用,省下钱还可以给女买点东西……」
我摇摇头说:「省什么?大不了我出去,里外一条命。」
丈夫突然著急起来,咳嗽更加剧烈,用手指著我说:「你!…别…呵呵…」激烈的咳嗽让他无法继续说话。
我急忙拍著他后背,哄著他说:「好了,好了,我说错了,我听你的,还不成?……来,吃点早点吧。」
我拿来早点,送到他面前。
他推开我的手,对我说:「不,先给女兒吃吧,我还不饿。」
我看看他,阳光照射在他脸上,30多岁的他满脸皱纹,好像有60多岁,长年累月的病痛已经把他折磨的不成样子,1米8的个头只剩下一把骨头,看著他的样子,我只觉得可怜,好容易不咳嗽了,丈夫闭上眼睛静静的躺下,喘息声逐渐均匀。我把生病的女儿从床上抱下来,放在凳子上,一口一口餵她早点,女儿忽然问:「妈,现在天亮了吗?」
我看看窗户外面,这时候雪已经完全停了,阳光照射在雪片上,发出刺眼的亮光。
我看著女儿,她的样子彷彿是我的翻版,鸭蛋脸,大眼睛,月牙眉,個子小巧,嘴巴大了点,惟独和我不一样的就是她那大大的眼睛里一片灰色,这孩子生下来就是病奄奄的,本来想给她看大夫的,可像我们这样的家,维持一个躺在床上的丈夫已经很勉强了,还谈给女儿看病?
我用手抚摩著女儿的头髮,长长的头髮散乱的搭在脸庞,我一边用手帮她拢著,一边餵给她豆包吃。我轻轻的说:「今天阴天,外面路灯还点著呢,快点吃吧。」
女儿空洞的大眼睛望著我,再也没说话。
餵饱了女儿,我把她抱到床上,她抱著那个破旧的布娃娃玩著。
事實上,我曾经在城里的夜总会里做小姐,那时候我正年轻,长得漂亮,身材也好,人浪,活儿翘,那时候追我的人太多了,但只要出得起钱,我向来不拒。后来,在一次例行的突击检查中,警察抄了夜总会,正赶上那晚我在2楼伺候客人,慌乱中我从2楼跳了下去,这一下就把腿给摔疼了,至今走路還得硬扭了屁股慢慢而行。
腿傷了修養幾個月以后,想不到我的价格大打折扣,从一个上流小姐,变成了三流小姐,价格便宜的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,不到百來块钱就能和我睡觉!我一气之下离开了夜总会,后来我又凭借老关係在城里几个大的夜总会坐了台,可惜,一直没什么起色,随著年岁增大,我逐渐萌生退意。就在这时,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,那时候他可帅了!自己又有一家小工厂,天天开车来,开车走,本来我自认为是个小姐,腿又不好,根本配不上他,可偏偏就这么怪,他竟然看上了我!经过几次交往,我们就过到了一起,我曾经问过他:「你难道不在乎我以前是个小姐?」他看看我说:「你以前怎么样,我不在乎,但你以后如果再敢出去做,我就把你打残,然后我再养你一辈子。」我忽然觉得找到了终生的依靠,发誓要好好的和他过日子。
甜蜜的日子最好过,一年以后,我们就添了一个寶貝女儿,可自从女儿诞生后,好像厄运就降临了,先是发现女儿的身體有毛病,到医院一检查,先天性心脏不好又弱视,视力茫茫。
为了给女儿治疗,我们跑了许多医院,花的钱象流水一样,最终也没什么结果。正在这时候,丈夫的工厂也开始衰败,销路不好,产品落后,工厂发不出工资。女儿的病再加上工厂的问题,丈夫的脾气也逐渐暴躁起来,整天喝酒,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,喝醉了动手就打我,我也只有默默忍受著。逐渐,家里的钱,存折都被丈夫拿走了,后来,连值钱的东西都被他拿出去卖了,工厂也倒闭了,我曾经试探著问了他几次,招来的只是一顿暴打,最后我也不敢问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天天喝酒沉沦,这点家底很快就花了精光呀!
没两年,我们连房子都卖了……
丈夫从医院里出来以后,把酒瘾是戒掉了,可开始咳嗽起来,一开始没注意,后来越来越厉害,到医院一检查,肺气肿,属于「酒精中毒症」之一,大夫将我叫到一旁,对我说:「可能会发生病变,75%,保守的说,很可能是肺癌……」
现在,只有我知道,吃那些药不过是维持他的生命而已,我经常对自己说:「只要能让他多活一天,我寧愿再去做小姐,哪怕他好了以后把我的腿打折打爆,我都認了…」
日头已经正当午时,女儿抱著布娃娃睡著了,丈夫也正睡得香,我站起来,轻轻的为他们盖好被子,摸摸口袋,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,我算了算,距离上次『低保』才半个月,每个月350块钱的低保根本不够家里的生活,更何况还有个得病的丈夫,生病的女儿。
我轻轻的走出门去,快速而小心的把门关好,透过窗户我看了看正在熟睡的他们,见没惊动,慢慢的走向胡同口。
地上都是雪,我慢慢的走著,出了胡同有一个公用电话亭,我拿起电话,拨通了一个号码……我的心里很复杂,脑子里只是想著能让丈夫再有钱买药,女儿以后还要上学,家还要过下去……
「喂?谁呀?」电话拨通了,从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我沉默了一会,说:「阿毛,是我。」
「你是谁呀?」阿毛怪声说。
我的怒气一下子顶到脑门上,突然大声说:「连我都听不出来了!想死呀你!!」我彷彿又回到了当年……
这次阿毛听出来了,惊叫了一声:「哦!是俞姐呀!!我他妈该死!连老姐都没听出来!我该死!俞姐,你……不是?」
我的心里痛快了一点,对阿毛说:「我找你有事,晚上,四平门。」
阿毛鸡鸡歪歪的说:「哎呀,老姐,我现在很忙……」
我还没等他说完,打断了他的线点前我要是没见到你,以后别让我遇到你,我跟你没完!」
阿毛停了一下,嘻嘻的说:「老姐,别生气呀,我说著玩的,行!晚上8点,四平门。」
阿毛是我的干弟弟,一个地痞,说白了,就是地头蛇,阿毛有点势力,罩著好几个场子,许多迪厅和夜总会都和他有关係,他认识的人也多。
我掛了电话,慢慢的回到家。
中午的午饭就是早点剩下来的东西,丈夫在我的劝导下,好歹吃了点,女儿也吃了点,给阿毛打过电话,我也觉得有点饿了,早点都给他们爷俩吃了,我翻了半天,只翻出半袋方便麵,凑合著吃了,只等晚上。
天渐渐的暗了下来,屋子里开始冷了,为了让他们更暖和一点,我用被子把他们捂得严严实实的,中午的饭里,丈夫沉沉的睡著。女儿也睡得很香。
我对著镜子照了照,把脸擦了擦,头髮拢了拢,还好,还可以看出一点熟女风采,毕竟我仍是个道地的村姑大妞樣兒,白嫩丰腴娇艳,豐滿的面頰,深黑的眼眉斜飛入鬢,蘊著英氣蕴藏敢爱敢恨任性歡喜就好的性格。小巧紅唇像石榴花汁濃得要滴要滴的,蘸一下未始不會染指成丹。我的笑容彩烂見於形,可掬可爱,魅态横生毫不含糊,嬌憨得尚有青春鮮烈的五官恭整,娥眉皓齿,天生一双迷迷媚眼配上二条湾湾秀眉,很是美艳动人,虽然年过三十,但无论从外貌还是身材看上去都是一个熟透的女人,端莊、嫻淑、優雅散发出来的高贵气质不是一般熟女能媲美的,说起体型呀,在眾女人中可属最标緻,最顶标的!高挑肉感身裁,三围34,28,37。如今虽然到了徐娘半老年纪,肢体依然匀称,肉肉翹臀,脸型是有一点的日本人与南*棒人混合形像,一站立在众女人堆里,似乎只剩我的脸孔其他女人都失色不见了。我的皮肤非常的细嫩雪白,手指,脚丫子也白白净净。姐就是特爱,特护养自己37号半美艳大脚和白玉雕般的白嫩脚趾头,脚趾甲剪了尖尖的,塗着透明光亮趾甲油,嫩白大脚板总搽点香水,好诱人,好迷人,只是我这一身衣服太寒了,黑色的裤子,还是丈夫穿剩下的,一双老式的皮暖靴恐怕扔在路边都没人要,还有,破旧的蓝色防寒服上面都是污渍。我知道,自己冬天的衣服就这么一件,没办法,凑合著吧。冬天的天黑得很早,刚过6点,天就黑了下来,我看看熟睡中的他们,慢慢的走出门。
四平门距离我的家很远,我只想慢慢的走著去。大街上,正是车水马龙热闹的时候,人多,车多,路灯已经亮起,把大街上照得很亮,远处高楼大厦的灯光为城市的夜晚增加了点缀,一片歌舞昇平的繁荣景色。我终于走到四平门的时候刚好8点,我一眼就看见正和几个小混混说话的阿毛,我喊了一声:「阿毛!」
阿毛高高的个子,头髮染成黄色,一身高级皮衣,手上带著金錶、金链子,耳朵上还带著耳环。听到我的叫声,阿毛突然一回头,一边衝著我走过来,一边仔细的看著我,一直走到我的跟前,又仔细的看看我,忽然说:「俞姐?你是俞姐?你?……噯呦!我的老姐呀!你怎么这样了!?没穿件像样衣裳?!」
跟著阿毛的几个小混混也跟著围过来,其中一个看看我,突然笑著说:「女要饭呀!……长了不赖,打一泡呗!」
还没等他说完,阿毛一回手给了那小子一个大嘴巴,那小子一愣,阿毛大吼著:「操你妈的!再放屁我他妈卸了你!滚!你们都给我滚远点!再往这凑合,我他妈可发火了!操你妈的!」几个小混混可能从来没见阿毛髮这么大的火,乖乖的退到一边去了。
阿毛拉著我又走了几步,到了路灯的昏暗处,问:「俞姐,你这么混成这样啦了?怎么混成这样了?前年我听他们说,你不是从良了吗?还弄了个款,怎,怎么这样了?」
说实话,我没什么亲人了,阿毛也可以算是我的一个亲人吧,见到阿毛,听他问话,我忽然觉得见到亲人,心口一热,眼泪再也止不住了,『呜呜』的哭了起来。
阿毛著急了,大声说:「怎么了你!老姐!原来你可从没掉过眼泪,怎么不爽了?说话呀!……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!哎!老姐,只要谁敢欺负咱,你告诉我名字,我他妈的三天之内卸了他!……」
我摇摇头,拉著他的手,慢慢的把这几年的经歷讲了出来。跟他说了将近一个多小时,阿毛才长长的出了口气,说:「哎呦!老姐,我说句实话,你可别不爱听,你的命呀,太苦了!」
……
随后,阿毛把那几个小混混叫过来,带著我走向繁华的闹市区……我本来不想做头髮的,可阿毛硬是拉著我到他的髮廊好好做了头髮,然后又给了我几件衣服,最后带著我去吃饭,阿毛对我说:「老姐,别的我帮不了你,也就是这样了,你看还有什么我能帮的?」
我看看阿毛,咬了咬牙,对他说:「我想挣钱,还是老本行,你帮我联繫联繫。」阿毛沉默了一会儿,看看我,对我说:「俞姐,说实话,那个罪你还没受够呀?」
我不说话,只是看著阿毛。
阿毛躲开我的目光,说:「行了。你想出来做,我会尽力的,不过老姐你也知道的,说实话,你这个岁数也大了点,身体又不好,别怪我说,恐怕即便有了人,这折腾妳现在受得了吗?皮肉钱也不会给很多,毕竟现在年纪轻,漂亮的小姐多的是,老姐,我这可是说实话在前头。」
我点点头,说:「我知道自己的条件,不过你帮我联繫就是了,你抽多少我不管。」
阿毛一瞪眼,大声说:「俞姐,你把看成什么人了?凭借咱们的关係,我还抽?抽他妈个屁!」
临走的时候,阿毛扔给我一个BP机,然后对我说:「有了,我呼你,地方我给你找。」
……
四平门,某旧楼独单。
房间里,我光著身子坐在凳子上,我的面前站著一个年轻男人,高高的挺著鸡巴,鸡巴又粗又长,直楞楞的,我用手搂著他的屁股,伸缩著头,用小嘴耐心的套弄著粗大的龟头,年轻男人仰著头,舒服的哼哼著,房间里暖气给的很热,我们的身上都见了汗。由於很久沒作,屄裡的浪水禁不住哗啦哗啦的流出来了。
我用手慢慢的摸著他的屁股,男人说:「月月,一会给我来来后面。」
我吐出鸡巴,抬头看看他,笑著说:「张哥,还是喜欢这个调调?」
张哥笑著说:「玩就玩个爽,要不还不如手淫呢。」
我笑了笑,继续低头唆了著他的鸡巴,张哥把我拉起来,拉到床边,他用手撑在床沿上撅起屁股,我跪在他的后面分开他的屁股,舔著屁眼,前面用手擼著他的鸡巴,张哥回手按住我的脑袋,使劲的把我的头按在他的屁股上,然后屁股上下的摩擦著,嘴里嘟囔著说:「哎呦!爽!使劲舔!…对!把舌头伸进去!…使点劲!……啊!」
张哥的屁眼真臭的,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?为了能多挣点钱,什么都要干。
我死命的舔著他的屁眼,用舌头挤进屁眼里抽插著,张哥快乐的呻吟著,鸡巴头上分泌出黏糊糊的淫液。
张哥突然扭过身,把鸡巴直接插进我的小嘴里快速的挺著屁股,鸡巴使劲的插进我的嗓子眼里,直到把我插得白眼直翻。张哥看著我可怜的模样,鸡巴终于挺到最佳硬度。
张哥把我拉到床上,戴好避孕套,鸡巴硬得好像铁棒一样,我趴在床上,高高的撅起肥硕的屁股,张哥趴在我身上,鸡巴一挺插了进去,然后快速的有节奏的抽插著,『啪啪啪啪……』鸡巴大力的撞击著我的屁股,浪里涌出大量的黏液,鸡巴更滑溜的进出著,张哥一边使劲操著,一边抓著我的头髮说:「爽!…骚!真浪!」
我浪浪的哼哼著,笑著说:「张哥…张哥…快!……操得我高潮来了!……快!啊!啊!啊!……啊!」
我紧紧的夹起腿,屁股玩命的使劲往后狂顶,张哥好像骑马一样在我的身上撒欢的操著,大叫著:「出来!……哦!……给我尿!使劲尿!」
「啊!……」我的大脑一阵发白,浑身一颤抖,久久憋著的一泡热尿『滋』的一下喷了出来,黄色的尿液喷撒在床上。
张哥见我的热尿被他操得喷了出来,更加激动起来,他把鸡巴插在里,一使劲就把我从床头拉到地上,我一拐一拐的在房间里慢慢的转著,张哥在后面继续使劲的操著,我一边转,一边还要撒尿,热热的尿液喷洒在地上。
张哥把鸡巴拔出来,我一阵晃动,差点没坐在地上,尿也撒完了还扎扎实实的泄了好几泡阴精。
张哥捏著鸡巴根,他的鸡巴颤抖著挺了好几下,差点没射出来,好不容易把这股劲压了下去,张哥大大喘息了一口气,用手拍拍我的屁股,说:「来,操屁眼。」
我站在房间的中央,微微分开腿,把两支手按在膝盖上使劲的低头撅屁股,张哥站在后面,分开我的屁股,露出屁眼,鸡巴对准以后,使劲的插了进去,一下就插到底!我『哎呦!』的叫了一声,张哥开始慢慢的前后晃动著屁股,硬硬的鸡巴在屁眼里开始进进出出起来。
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……』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……』鸡巴乾燥的在我的屁眼里进来出去,张哥一下子把鸡巴抽出来,转到我的面前,鸡巴一挺,对我说:「来,使劲唆了两口,多弄点唾沫。」
我一抬头,一张嘴,一口把又臭又骚难闻的大鸡巴叼住,大力的吸吮著,张哥受到刺激,鸡巴使劲的在小嘴里又狠插了两下,拔了出来。我衝著鸡巴吐了两口唾沫,张哥重新来到我的背后,鸡巴再次插了进来,这次,张哥更加快速的操著屁眼,我也浪浪的叫著春:「啊!啊!!啊!张哥!好棒!痛快!……哎呦!哎呦!哎呦!……使劲操!使劲呀!」
张哥扶著我的屁股,快速的用鸡巴操著,大鸡巴经过唾液的润滑,在屁眼里滑溜的伸缩著,我只觉得屁眼里阵阵的鬱闷,一下一下使劲的缩著屁眼,夹住鸡巴而蜜穴的浪水留个不停。
张哥狠狠的操了两下,抽出鸡巴,拉著我来到床铺上,我自觉的躺在床上,把头搭在床沿,张哥擼掉避孕套,一抬腿,骑到我胸脯上,用手捏著我的乳头,鸡巴使劲的插进我的小嘴里,快速的一阵狠操,突然惊叫一声『呦!……』,突突的射出白花花的精液来。
他一边快速的擼弄著鸡巴,一边对著我张开的小嘴喷射著,白色的精液喷洒在我的舌头上,我只笑嘻嘻的看著他,直到他再也射不出来了,我才『咕咚』一下把精液嚥了下去……
操完以后已经全身乏力瘫痪了,我勉强扶著张哥在厕所里洗了个热水澡,男人爽了身子,又洗了热水澡,顿时精神焕发,他穿好厚厚的衣服,拢拢头,然后从钱包里掏出几张大票,塞进我的手里,笑著说:「下次我过来的时候先给你传呼。」
我笑著点点钱,乐著说:「谢谢大哥了!每次都多给!下次您再来,一定给我打传呼,下次再来呀!」
我把张哥送走,一边点著钱,一边合计著怎么分配。然后又接了个彝族汉子,四十余岁,身高接近一米九,鸡巴很长,他又黑又高又瘦,还有些脏。我不喜欢他,但是他固执地要点我,他是客人,我只好接待他。他只喜欢一种姿势,让我站在房中间,他用胳膊抬起我的一条美腿,亮出屄眼,他让我搂住他的脖子,他抱着我,狠狠地挑射我。他的鸡巴很长,捅得我很酸很痛。我不喜欢这个脏家伙,于是生气道:「好痛啊,不来了!」但是那彝族汉子力气很大,被他紧紧抱住,挣脱不得,只好任他发泄。他一边操,还一边摸我的奶子,还要我设法站好,自己捧抱着二颗大奶,人不停的蠕动身体,整片臀部都是湿亮的汗汁。尽仅剩的一点力气紧紧夹紧肛门更使劲的打开腿缝,我女性的矜持早已被排山倒海的肉欲所淹没。我的陰核慢慢的变大从包皮中翘起而富有弹性,汉子知道时机已成熟,改以只手指轻轻的抠抚我的湿滑肉沟子。「很好!看妳怎么逃?毛在尿孔里!嘿嘿!」这会可真尽情的玩弄妈妈的尿道。彝族汉子用指甲去剥开尿孔,随手取个菜根,绕尖去碰触到尿孔更深的地方,尿道壁的嫩肉像鱼嘴一样的开合,接着热腾腾的淫汁加上骚尿一滴滴顺了菜根流出来滴在地上。「嗯…嗯…哦…哦… 」我抬着屁股迎合著,「啊哟……阿唷喂哦!」我激烈的挺腰哀吟,强烈的快感快速的麻痹敏感的身体,一阵昏晕,鬓髮全散卧倒在地。那种让人丧失神智的痒痒痛痛,令我的隂道不断抽稸啦,屄屁潮吹连连呀,可比死去还要痛苦羞愤啊!直到操了二十分钟,他射了,才放开我。以这个姿势被他操二十多分钟,我腰痛背酸,操完走都不稳啦。完事后,我快速的穿上衣服,飞奔医院。
……
自从上次见过阿毛后,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,这些天,我没日没夜的干,前前后后,吃足嫖客苦头,希望弄了点钱把丈夫送进了好点医院,生病的女儿我托付给了阿毛,阿毛把她送到了阿毛的姥姥家,我曾经去看过,那是个很好的老太太,我放心。可是丈夫的身体越来越不好,虽然进了医院,但我们只能住普通病房,丈夫咳嗽得越来越厉害,已经开始见红了,医生不只一次的严肃对我说,要我有个心理准备,因为他的肺气肿时间太长了,已经发生病变,估计可能是肺癌,最省钱的治疗也是每週两次的放化疗,钱太多了,已经上万,我支付不起呀!只能勉强在医院耗著,能让他多活一天都好。我到了医院,先是到住院处把这几天积攒的钱交给了会计,然后到食堂买了点吃的,送到丈夫的病房里,阿毛真的很好,特别交代了他手下的两个小混混在医院里守著。进了门,那两个小混混站起来,很规矩的叫了声『俞姐』然后就出去了。我看著满身插满管子的丈夫,子一,眼泪差点没掉出来。或许是丈夫有了心灵感应,他竟然睁开了眼,看到我,丈夫也一裂嘴,他想哭,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,只是干干的泣著。
我见他醒了,赶忙擦乾眼泪,小声的问他:「想吃点东西吗?」
丈夫闭上眼睛轻轻的摇摇头,然后又睁眼看著我,我坐在他身边,抓著他的手,一言不发的和他对视著,我们就这么静静的互相看著,一切都在眼神里表达出来。
外面的西北风又『呜呜』的刮了起来,彷彿是在悲,大风带来了雨雪,散落的雪花随著狂风漫天飞舞,城市的夜晚降临了,病房里很安静,彷彿时间凝固了,就在这城市被遗忘的角落里,有我,还有我的丈夫。
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,已是晚上7点。BP机响了起来,我赶忙去回电话。
「俞姐,我介绍了两个朋友到你那里去,一会见。」阿毛的话很简洁。
我放下电话,赶回四平门。阿毛热情的替我引见两个客人,一个姓张,张老闆,个子中等,30多岁,不胖,很有文化的样子,穿著时。另一个姓许,许老闆,个子比张老闆矮点,30多岁,胖乎乎的满面笑容,穿著讲究得体。
我送阿毛出去的时候,阿毛忽然小声对我说:「他们,捻子(钱)多,照到位了(伺候好了)。」
我点点头。
锁好门,我笑著对他们说:「两位老闆,别客气呀,坐呀。」
我一边说著,一边走到他们中间,慢慢的脱著衣服,许老闆很老道,笑著说:「大姐好爽朗哦!侍候我们,可得开放搞活哟!」
我笑著说:「咳,行!行!!您二位都是阿毛的朋友,不是外人,我也就不和您上俗套了,大家出来玩,不就是图个乐和吗?来,我帮您脱衣服。」
说完,我帮著张、许二人把衣服脱了,我仔细一看,两个人身上都是白白净净的,鸡巴也乾净,不大不小很适中,我拉著他们坐到床上,慢慢的捻著他们的鸡巴,笑著说:「噯呦!好大的货哦!许老闆,您的鸡巴真够个儿!」
他们二人的手在我身上乱摸著,许老闆乐呵呵的说:「大姐,别捧我!我识得的。」
我对张老闆笑著说:「哎呀!张老闆,您的鸡巴也不小呀!」说完,我对他们说:「说老实话!我干了这么多年,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个的鸡巴!又粗又长!一会操起来肯定带劲儿!」
张老闆和许老闆在我小手的擼弄下,鸡巴已逐渐挺起,我一边擼弄著鸡巴,一边让他们的手在我的乳房和浪上紧摸著,我一边有感觉的小声哼哼,一边浪浪的道:「我说,二位老闆,咱们谁先上?我这儿可刺痒著呢!要不,咱们开个洋荤,也学学老外,玩个三人行什么的……一个插浪屄,一个杵屁眼,然后,我再给您唆了唆了大鸡巴,让您美美的把精子射出来!怎么样?」
张老闆嘻嘻的笑了,对我说:「阿毛早就和我们说,大姐的人浪,活翘,今儿我们来,还就是为玩这个来的!来!」
张老闆和许老闆分别带好避孕套,张老闆躺在床上,我对著他挺起的鸡巴吐了口唾沫,用手猛擼了两下,然后跨到他的身上,鸡巴对准浪使劲坐了下去,张老闆舒服的哼出了声。
我将鸡巴连根坐进里,屁股前后小范围的伸缩著,转头对著许老闆的鸡巴吐唾沫,等鸡巴润滑了,我拉著鸡巴顶在屁眼上,许老闆骑在我的屁股上,慢慢的把鸡巴插进屁眼,等鸡巴都到位了,我忽然大声的哼了出来,『操!』张老闆和许老闆同时挺起屁股,一时间,房间里嘈杂起来……
「嘿!嘿!嘿!嘿!…」许老闆快速的前后运动著屁股,粗大的鸡巴在屁眼里抽插,黏糊糊的肛油加速了鸡巴的润滑,许老闆看著小屁眼被鸡巴操得乱翻,撒欢的插了起来。
「哎!哎!哎!哎!……」张老闆在下面一边使劲的揉弄著我的乳房,一边看著我浪浪的样子,大力的往上挺屁股,希里黏糊糊的淫液弄得他特别爽,张老闆激动的操著。
「发!……呀!……爷!……天!……哦!……啊!」我一边摇晃著头,一边胡乱的叫嚷著,前后夹击的刺激,让我头脑里一片空白,这活也真不是人干的。
『扑!』的一下,许老闆从屁眼里拔出鸡巴,鸡巴在空气中高挺了两下,许老闆呼呼的喘著粗气,一把把避孕套擼了下来,说:「好玄!屁眼太紧了!差点把套子搓破了。」
说完,许老闆用手指伸到我的屁眼里抠著,然后看著张老闆说:「你来玩玩这,油都出来了!」
张老闆一把把我推开,许老闆重新带上一个新的避孕套躺在床上,我跨在许老闆的身上,张老闆在后面插屁眼。
这个三人行足足玩了将近半小时,许老闆突然紧张的说:「我……我要来!躲开!」
说完,他大力的把我推到一边,张老闆也闪开,许老闆按住我的屁股,颤抖著手捏著鸡巴插进屁眼,然后玩命的使劲操著,屁股一下比一下快!
我知道他就快射精了,也急忙淫叫起来:「啊!啊!屁眼!啊!啊!屁眼破啦!我可憐的小屁眼被你捅破啦,喔,痛唷喔,裂開啦!啊!啊!」
在我一声声屁眼的乱叫声中,许老闆抽出鸡巴,快速的擼掉避孕套,我急忙起身含住他的鸡巴头,许老闆大叫一声「爽!」,鸡巴在我的小嘴里射出热热的精子!逼了我吞下了肚。
与此同时,张老闆赶忙将鸡巴塞进我的屁眼里抓紧操著,我刚刚嚥下许老闆的精液,再次大声的叫嚷起来:「噯呦!痛快!啊!啊!啊!啊!!」伴随著我最后一声淫叫,张老闆还没等把鸡巴抽出来就射精了,他死命的按著我的屁股,鸡巴插进屁眼里一动不动,我只觉得屁眼里的鸡巴扩大好几倍,一阵乱挺,火热的精子射了出来!
高潮以后,张老闆和许老闆穿好衣服,许老闆淫笑著对张老闆说:「你还是不行呀!还没抽出来就放炮了!」
张老闆也不甘示弱的说:「别管怎么说,我比你放炮放的晚,嘿嘿。」
两个男人互相打趣著。
我笑著伸出双手的大拇指说:「两位老闆都很强!很棒!操屁眼能操到这个程度的,就属您二位了!」
张老闆笑著说:「大姐,再怎么说,没有你这个小屁眼,我们也没这么爽!哈哈哈!」
我和许老闆也跟著笑起来。
许老闆站起来,从钱夹里拿出几张大票塞进我手里,乐呵呵的说:「下次还找你!嘿嘿。」
我点了一下钱,真不少!急忙浪浪的笑著说:「许老闆!看您说的!干嘛下次呀!这次不好吗?要不,咱们再点两炮?…」说完,我小声的对他们说:「哎呀!第一次,咱们玩的规矩,要是知道您二位是那么爽快的人儿,咱们玩点儿脏活儿,那才叫爽呢!」
张老闆眼睛一亮,淫笑著说:「什么活儿?」
我笑瞇瞇的说:「不带套子跑旱船,然后给您来个活叼,放炮以后,还给您用小嘴唆了个乾净……」
张老闆跃跃欲试就想上,许老闆一拽他,笑著对他说:「忘了!还有饭局呢!」
一句话提醒了张老闆,张老闆满脸惋惜的说:「算了,算了!下次再玩吧。」
我见没什么希望,转脸笑著说:「没关係,我还能跑了不成?早晚让您大爺爽個夠!」
张老闆和许老闆客气的笑了笑,向门外走去。
送走了他们,我穿好衣服,准备给自己弄点吃的,这时BP机又响了起来,我心说:阿毛真好,又有生意了。但是我的小屄卻抗議了,「吃不消啦,今天已經被姦了好幾回,酸酸痛痛,再也經不起折騰啦!」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丈夫已经整整昏迷两天了,医生把我叫出去,只对我说了一句话:准备准备吧,别到时候……后面的话我根本没听见。
连日的接客疲劳,我靠在丈夫的旁边昏昏的迷糊。
突然,我觉得有人碰我,我激灵一下坐了起来,只见丈夫竟然睁开眼,看著我,我急忙凑过去,小声的问:「饿吗?」丈夫摇摇头,我继续问:「渴吗?」
丈夫使劲的对我说:「咱女儿呢?我想看看。」
我装著笑,说:「快过年了,我把她送到一个姥姥那儿去了,那很好,有暖气,有好多好吃的,饿不著她……」下面的话,我实在编不出来了,眼泪几乎掉了下来。
丈夫的声音忽然清晰起来,他看看外面灰的天空,嘴里嘮叨著:「哦,快过年了……女儿别饿著……别冻著……过年了……快过年了……」
丈夫好像很睏,慢慢的闭上眼睛,突然,他又睁开眼,瞪大眼睛仔细的看著我,对我说:「哦,对了,还有个事儿,以后,不管怎么苦,你也别出去做了!好好照顾女儿,听我一句吧……」说完,丈夫缓缓的闭上眼睛,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,瞬间流了下来!丈夫就这么走了,撇下我……
过年了!大街上热闹起来,人们的脸上喜气洋洋,到处热闹非凡,电视里,电台里,到处是欢声笑语,鞭炮声,笑声,唱歌声,一片欢乐……
我还是穿著那身破旧的衣服,一瘸一拐的走在路边,慢慢的拐进了小胡同,慢慢的走进我那间破房子,屋里好冷呀!外面的天空还是那么混沌,灰灰的。
我和衣躺在床上,摸到了女儿的那个破旧的布娃娃,我把它抱在怀里,彷彿女儿在我的怀里,轻轻的拍著,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药瓶,颤抖著拧开盖子,把药片到进手心,一粒粒的放进嘴里,把那苦涩而冰冷的药片仔细的嚼碎,慢慢的嚥下去,心里想著:吃吧,吃吧,吃完以后,就能见到丈夫了,还有女儿……
啊!我好累哦,好困!我想好好的休息,好好的睡一觉,一觉醒来,没有了寒冷,没有了飢饿……我死死的抓著那个布娃娃……抱著它……
忽然间……
天空彷彿放亮……
大地一片明媚……一片广阔的天地……没有了飢饿……没有了寒冷……到处是绿茸茸的草地,到处是盛开的花朵……
我又看到了丈夫,他微笑著招呼著我,怀里抱著女儿……我扑向他们……紧紧的拥抱在一起……
跳呀!笑呀!……
跳呀!笑呀!……
北国,隆冬,大雪纷飞。
如果過的是和自己身分不相稱的生活,我就會時時感覺自己站的地方是傾斜的,於是經常要努力調整姿勢,擺一個和傾斜的地面相應的角度,如此才能保持站立的姿態……我的焦慮往往準時萌生。不管在什麼地方,不管正在做什麼事,天黑一到,就立即感覺到一股悶悶的,很難形容的焦慮的痛覺發自胃的底部,一點一點爬上來,向左滲透,向右擴散,終至感覺到整個胃又硬又重,像一塊巨石般盤踞在身體的正中央。晚上,焦慮中丈夫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,整夜整夜的咳,吃过药反而更加激烈。屋子里,我不敢生炉子,害怕烟气呛著他,生病的女儿因为寒冷,只是蜷缩在床脚瑟瑟发抖,我问她什么都不说。临家的奶奶心眼好,大早晨就送来一壶开水,我忙活著为丈夫倒水,多少能帮他暖和一点。
清晨,当一缕阳光从房间里破旧的窗户照射进来的时候,丈夫的咳嗽突然停了下来,他喘息著对我说:「老婆,给孩子弄点吃的吧,别饿著她。」说完,丈夫躺下去,闭上眼睛。我点点头,穿上棉衣走出门去。门一打开,外面的雪花就吹了进来,我赶忙走出去把门关好。啊!天气真冷啊!天地彷彿被冻得凝固,到处是一片白色。胡同里也逐渐开始有了声气,家家户户开始了一天的忙碌,烟囱里冒出阵阵的轻烟,配合著这浑然的白色,别有一番景象。
在胡同口就有叫卖的小摊,油条、豆浆、小米粥、豆包……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。
我虛弱的一步一步走到胡同口,小摊前面稀稀拉拉的有几个买早点的人。
「一碗小豆粥,两个豆包,两根油条。」我掏出一块五角钱递过去。
「两元!油涨 了。」满身油渍的老闆说。
我犹豫了一下,又再掏出五毛钱给他。
他抬头看看我,然后把东西包好,递到我的手里,对我说:「你慢点走,道路滑。」
我没说什么,捧著东西一步步走回家去。
回家以后,急忙把东西分开,小豆粥、豆包、油条都分成两份,生病的女儿闻到了香气也摸著床槓爬了过来,丈夫又开始咳嗽起来。我走过去,帮著他坐在床上,一边拍著他的后背,一边说:「吃点东西吧?唉,怎么这么咳呢?」
丈夫说:「呵呵……别吃那药了,吃了也没用,省下钱还可以给女买点东西……」
我摇摇头说:「省什么?大不了我出去,里外一条命。」
丈夫突然著急起来,咳嗽更加剧烈,用手指著我说:「你!…别…呵呵…」激烈的咳嗽让他无法继续说话。
我急忙拍著他后背,哄著他说:「好了,好了,我说错了,我听你的,还不成?……来,吃点早点吧。」
我拿来早点,送到他面前。
他推开我的手,对我说:「不,先给女兒吃吧,我还不饿。」
我看看他,阳光照射在他脸上,30多岁的他满脸皱纹,好像有60多岁,长年累月的病痛已经把他折磨的不成样子,1米8的个头只剩下一把骨头,看著他的样子,我只觉得可怜,好容易不咳嗽了,丈夫闭上眼睛静静的躺下,喘息声逐渐均匀。我把生病的女儿从床上抱下来,放在凳子上,一口一口餵她早点,女儿忽然问:「妈,现在天亮了吗?」
我看看窗户外面,这时候雪已经完全停了,阳光照射在雪片上,发出刺眼的亮光。
我看著女儿,她的样子彷彿是我的翻版,鸭蛋脸,大眼睛,月牙眉,個子小巧,嘴巴大了点,惟独和我不一样的就是她那大大的眼睛里一片灰色,这孩子生下来就是病奄奄的,本来想给她看大夫的,可像我们这样的家,维持一个躺在床上的丈夫已经很勉强了,还谈给女儿看病?
我用手抚摩著女儿的头髮,长长的头髮散乱的搭在脸庞,我一边用手帮她拢著,一边餵给她豆包吃。我轻轻的说:「今天阴天,外面路灯还点著呢,快点吃吧。」
女儿空洞的大眼睛望著我,再也没说话。
餵饱了女儿,我把她抱到床上,她抱著那个破旧的布娃娃玩著。
事實上,我曾经在城里的夜总会里做小姐,那时候我正年轻,长得漂亮,身材也好,人浪,活儿翘,那时候追我的人太多了,但只要出得起钱,我向来不拒。后来,在一次例行的突击检查中,警察抄了夜总会,正赶上那晚我在2楼伺候客人,慌乱中我从2楼跳了下去,这一下就把腿给摔疼了,至今走路還得硬扭了屁股慢慢而行。
腿傷了修養幾個月以后,想不到我的价格大打折扣,从一个上流小姐,变成了三流小姐,价格便宜的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,不到百來块钱就能和我睡觉!我一气之下离开了夜总会,后来我又凭借老关係在城里几个大的夜总会坐了台,可惜,一直没什么起色,随著年岁增大,我逐渐萌生退意。就在这时,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,那时候他可帅了!自己又有一家小工厂,天天开车来,开车走,本来我自认为是个小姐,腿又不好,根本配不上他,可偏偏就这么怪,他竟然看上了我!经过几次交往,我们就过到了一起,我曾经问过他:「你难道不在乎我以前是个小姐?」他看看我说:「你以前怎么样,我不在乎,但你以后如果再敢出去做,我就把你打残,然后我再养你一辈子。」我忽然觉得找到了终生的依靠,发誓要好好的和他过日子。
甜蜜的日子最好过,一年以后,我们就添了一个寶貝女儿,可自从女儿诞生后,好像厄运就降临了,先是发现女儿的身體有毛病,到医院一检查,先天性心脏不好又弱视,视力茫茫。
为了给女儿治疗,我们跑了许多医院,花的钱象流水一样,最终也没什么结果。正在这时候,丈夫的工厂也开始衰败,销路不好,产品落后,工厂发不出工资。女儿的病再加上工厂的问题,丈夫的脾气也逐渐暴躁起来,整天喝酒,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,喝醉了动手就打我,我也只有默默忍受著。逐渐,家里的钱,存折都被丈夫拿走了,后来,连值钱的东西都被他拿出去卖了,工厂也倒闭了,我曾经试探著问了他几次,招来的只是一顿暴打,最后我也不敢问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天天喝酒沉沦,这点家底很快就花了精光呀!
没两年,我们连房子都卖了……
丈夫从医院里出来以后,把酒瘾是戒掉了,可开始咳嗽起来,一开始没注意,后来越来越厉害,到医院一检查,肺气肿,属于「酒精中毒症」之一,大夫将我叫到一旁,对我说:「可能会发生病变,75%,保守的说,很可能是肺癌……」
现在,只有我知道,吃那些药不过是维持他的生命而已,我经常对自己说:「只要能让他多活一天,我寧愿再去做小姐,哪怕他好了以后把我的腿打折打爆,我都認了…」
日头已经正当午时,女儿抱著布娃娃睡著了,丈夫也正睡得香,我站起来,轻轻的为他们盖好被子,摸摸口袋,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,我算了算,距离上次『低保』才半个月,每个月350块钱的低保根本不够家里的生活,更何况还有个得病的丈夫,生病的女儿。
我轻轻的走出门去,快速而小心的把门关好,透过窗户我看了看正在熟睡的他们,见没惊动,慢慢的走向胡同口。
地上都是雪,我慢慢的走著,出了胡同有一个公用电话亭,我拿起电话,拨通了一个号码……我的心里很复杂,脑子里只是想著能让丈夫再有钱买药,女儿以后还要上学,家还要过下去……
「喂?谁呀?」电话拨通了,从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我沉默了一会,说:「阿毛,是我。」
「你是谁呀?」阿毛怪声说。
我的怒气一下子顶到脑门上,突然大声说:「连我都听不出来了!想死呀你!!」我彷彿又回到了当年……
这次阿毛听出来了,惊叫了一声:「哦!是俞姐呀!!我他妈该死!连老姐都没听出来!我该死!俞姐,你……不是?」
我的心里痛快了一点,对阿毛说:「我找你有事,晚上,四平门。」
阿毛鸡鸡歪歪的说:「哎呀,老姐,我现在很忙……」
我还没等他说完,打断了他的线点前我要是没见到你,以后别让我遇到你,我跟你没完!」
阿毛停了一下,嘻嘻的说:「老姐,别生气呀,我说著玩的,行!晚上8点,四平门。」
阿毛是我的干弟弟,一个地痞,说白了,就是地头蛇,阿毛有点势力,罩著好几个场子,许多迪厅和夜总会都和他有关係,他认识的人也多。
我掛了电话,慢慢的回到家。
中午的午饭就是早点剩下来的东西,丈夫在我的劝导下,好歹吃了点,女儿也吃了点,给阿毛打过电话,我也觉得有点饿了,早点都给他们爷俩吃了,我翻了半天,只翻出半袋方便麵,凑合著吃了,只等晚上。
天渐渐的暗了下来,屋子里开始冷了,为了让他们更暖和一点,我用被子把他们捂得严严实实的,中午的饭里,丈夫沉沉的睡著。女儿也睡得很香。
我对著镜子照了照,把脸擦了擦,头髮拢了拢,还好,还可以看出一点熟女风采,毕竟我仍是个道地的村姑大妞樣兒,白嫩丰腴娇艳,豐滿的面頰,深黑的眼眉斜飛入鬢,蘊著英氣蕴藏敢爱敢恨任性歡喜就好的性格。小巧紅唇像石榴花汁濃得要滴要滴的,蘸一下未始不會染指成丹。我的笑容彩烂見於形,可掬可爱,魅态横生毫不含糊,嬌憨得尚有青春鮮烈的五官恭整,娥眉皓齿,天生一双迷迷媚眼配上二条湾湾秀眉,很是美艳动人,虽然年过三十,但无论从外貌还是身材看上去都是一个熟透的女人,端莊、嫻淑、優雅散发出来的高贵气质不是一般熟女能媲美的,说起体型呀,在眾女人中可属最标緻,最顶标的!高挑肉感身裁,三围34,28,37。如今虽然到了徐娘半老年纪,肢体依然匀称,肉肉翹臀,脸型是有一点的日本人与南*棒人混合形像,一站立在众女人堆里,似乎只剩我的脸孔其他女人都失色不见了。我的皮肤非常的细嫩雪白,手指,脚丫子也白白净净。姐就是特爱,特护养自己37号半美艳大脚和白玉雕般的白嫩脚趾头,脚趾甲剪了尖尖的,塗着透明光亮趾甲油,嫩白大脚板总搽点香水,好诱人,好迷人,只是我这一身衣服太寒了,黑色的裤子,还是丈夫穿剩下的,一双老式的皮暖靴恐怕扔在路边都没人要,还有,破旧的蓝色防寒服上面都是污渍。我知道,自己冬天的衣服就这么一件,没办法,凑合著吧。冬天的天黑得很早,刚过6点,天就黑了下来,我看看熟睡中的他们,慢慢的走出门。
四平门距离我的家很远,我只想慢慢的走著去。大街上,正是车水马龙热闹的时候,人多,车多,路灯已经亮起,把大街上照得很亮,远处高楼大厦的灯光为城市的夜晚增加了点缀,一片歌舞昇平的繁荣景色。我终于走到四平门的时候刚好8点,我一眼就看见正和几个小混混说话的阿毛,我喊了一声:「阿毛!」
阿毛高高的个子,头髮染成黄色,一身高级皮衣,手上带著金錶、金链子,耳朵上还带著耳环。听到我的叫声,阿毛突然一回头,一边衝著我走过来,一边仔细的看著我,一直走到我的跟前,又仔细的看看我,忽然说:「俞姐?你是俞姐?你?……噯呦!我的老姐呀!你怎么这样了!?没穿件像样衣裳?!」
跟著阿毛的几个小混混也跟著围过来,其中一个看看我,突然笑著说:「女要饭呀!……长了不赖,打一泡呗!」
还没等他说完,阿毛一回手给了那小子一个大嘴巴,那小子一愣,阿毛大吼著:「操你妈的!再放屁我他妈卸了你!滚!你们都给我滚远点!再往这凑合,我他妈可发火了!操你妈的!」几个小混混可能从来没见阿毛髮这么大的火,乖乖的退到一边去了。
阿毛拉著我又走了几步,到了路灯的昏暗处,问:「俞姐,你这么混成这样啦了?怎么混成这样了?前年我听他们说,你不是从良了吗?还弄了个款,怎,怎么这样了?」
说实话,我没什么亲人了,阿毛也可以算是我的一个亲人吧,见到阿毛,听他问话,我忽然觉得见到亲人,心口一热,眼泪再也止不住了,『呜呜』的哭了起来。
阿毛著急了,大声说:「怎么了你!老姐!原来你可从没掉过眼泪,怎么不爽了?说话呀!……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!哎!老姐,只要谁敢欺负咱,你告诉我名字,我他妈的三天之内卸了他!……」
我摇摇头,拉著他的手,慢慢的把这几年的经歷讲了出来。跟他说了将近一个多小时,阿毛才长长的出了口气,说:「哎呦!老姐,我说句实话,你可别不爱听,你的命呀,太苦了!」
……
随后,阿毛把那几个小混混叫过来,带著我走向繁华的闹市区……我本来不想做头髮的,可阿毛硬是拉著我到他的髮廊好好做了头髮,然后又给了我几件衣服,最后带著我去吃饭,阿毛对我说:「老姐,别的我帮不了你,也就是这样了,你看还有什么我能帮的?」
我看看阿毛,咬了咬牙,对他说:「我想挣钱,还是老本行,你帮我联繫联繫。」阿毛沉默了一会儿,看看我,对我说:「俞姐,说实话,那个罪你还没受够呀?」
我不说话,只是看著阿毛。
阿毛躲开我的目光,说:「行了。你想出来做,我会尽力的,不过老姐你也知道的,说实话,你这个岁数也大了点,身体又不好,别怪我说,恐怕即便有了人,这折腾妳现在受得了吗?皮肉钱也不会给很多,毕竟现在年纪轻,漂亮的小姐多的是,老姐,我这可是说实话在前头。」
我点点头,说:「我知道自己的条件,不过你帮我联繫就是了,你抽多少我不管。」
阿毛一瞪眼,大声说:「俞姐,你把看成什么人了?凭借咱们的关係,我还抽?抽他妈个屁!」
临走的时候,阿毛扔给我一个BP机,然后对我说:「有了,我呼你,地方我给你找。」
……
四平门,某旧楼独单。
房间里,我光著身子坐在凳子上,我的面前站著一个年轻男人,高高的挺著鸡巴,鸡巴又粗又长,直楞楞的,我用手搂著他的屁股,伸缩著头,用小嘴耐心的套弄著粗大的龟头,年轻男人仰著头,舒服的哼哼著,房间里暖气给的很热,我们的身上都见了汗。由於很久沒作,屄裡的浪水禁不住哗啦哗啦的流出来了。
我用手慢慢的摸著他的屁股,男人说:「月月,一会给我来来后面。」
我吐出鸡巴,抬头看看他,笑著说:「张哥,还是喜欢这个调调?」
张哥笑著说:「玩就玩个爽,要不还不如手淫呢。」
我笑了笑,继续低头唆了著他的鸡巴,张哥把我拉起来,拉到床边,他用手撑在床沿上撅起屁股,我跪在他的后面分开他的屁股,舔著屁眼,前面用手擼著他的鸡巴,张哥回手按住我的脑袋,使劲的把我的头按在他的屁股上,然后屁股上下的摩擦著,嘴里嘟囔著说:「哎呦!爽!使劲舔!…对!把舌头伸进去!…使点劲!……啊!」
张哥的屁眼真臭的,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?为了能多挣点钱,什么都要干。
我死命的舔著他的屁眼,用舌头挤进屁眼里抽插著,张哥快乐的呻吟著,鸡巴头上分泌出黏糊糊的淫液。
张哥突然扭过身,把鸡巴直接插进我的小嘴里快速的挺著屁股,鸡巴使劲的插进我的嗓子眼里,直到把我插得白眼直翻。张哥看著我可怜的模样,鸡巴终于挺到最佳硬度。
张哥把我拉到床上,戴好避孕套,鸡巴硬得好像铁棒一样,我趴在床上,高高的撅起肥硕的屁股,张哥趴在我身上,鸡巴一挺插了进去,然后快速的有节奏的抽插著,『啪啪啪啪……』鸡巴大力的撞击著我的屁股,浪里涌出大量的黏液,鸡巴更滑溜的进出著,张哥一边使劲操著,一边抓著我的头髮说:「爽!…骚!真浪!」
我浪浪的哼哼著,笑著说:「张哥…张哥…快!……操得我高潮来了!……快!啊!啊!啊!……啊!」
我紧紧的夹起腿,屁股玩命的使劲往后狂顶,张哥好像骑马一样在我的身上撒欢的操著,大叫著:「出来!……哦!……给我尿!使劲尿!」
「啊!……」我的大脑一阵发白,浑身一颤抖,久久憋著的一泡热尿『滋』的一下喷了出来,黄色的尿液喷撒在床上。
张哥见我的热尿被他操得喷了出来,更加激动起来,他把鸡巴插在里,一使劲就把我从床头拉到地上,我一拐一拐的在房间里慢慢的转著,张哥在后面继续使劲的操著,我一边转,一边还要撒尿,热热的尿液喷洒在地上。
张哥把鸡巴拔出来,我一阵晃动,差点没坐在地上,尿也撒完了还扎扎实实的泄了好几泡阴精。
张哥捏著鸡巴根,他的鸡巴颤抖著挺了好几下,差点没射出来,好不容易把这股劲压了下去,张哥大大喘息了一口气,用手拍拍我的屁股,说:「来,操屁眼。」
我站在房间的中央,微微分开腿,把两支手按在膝盖上使劲的低头撅屁股,张哥站在后面,分开我的屁股,露出屁眼,鸡巴对准以后,使劲的插了进去,一下就插到底!我『哎呦!』的叫了一声,张哥开始慢慢的前后晃动著屁股,硬硬的鸡巴在屁眼里开始进进出出起来。
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……』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……』鸡巴乾燥的在我的屁眼里进来出去,张哥一下子把鸡巴抽出来,转到我的面前,鸡巴一挺,对我说:「来,使劲唆了两口,多弄点唾沫。」
我一抬头,一张嘴,一口把又臭又骚难闻的大鸡巴叼住,大力的吸吮著,张哥受到刺激,鸡巴使劲的在小嘴里又狠插了两下,拔了出来。我衝著鸡巴吐了两口唾沫,张哥重新来到我的背后,鸡巴再次插了进来,这次,张哥更加快速的操著屁眼,我也浪浪的叫著春:「啊!啊!!啊!张哥!好棒!痛快!……哎呦!哎呦!哎呦!……使劲操!使劲呀!」
张哥扶著我的屁股,快速的用鸡巴操著,大鸡巴经过唾液的润滑,在屁眼里滑溜的伸缩著,我只觉得屁眼里阵阵的鬱闷,一下一下使劲的缩著屁眼,夹住鸡巴而蜜穴的浪水留个不停。
张哥狠狠的操了两下,抽出鸡巴,拉著我来到床铺上,我自觉的躺在床上,把头搭在床沿,张哥擼掉避孕套,一抬腿,骑到我胸脯上,用手捏著我的乳头,鸡巴使劲的插进我的小嘴里,快速的一阵狠操,突然惊叫一声『呦!……』,突突的射出白花花的精液来。
他一边快速的擼弄著鸡巴,一边对著我张开的小嘴喷射著,白色的精液喷洒在我的舌头上,我只笑嘻嘻的看著他,直到他再也射不出来了,我才『咕咚』一下把精液嚥了下去……
操完以后已经全身乏力瘫痪了,我勉强扶著张哥在厕所里洗了个热水澡,男人爽了身子,又洗了热水澡,顿时精神焕发,他穿好厚厚的衣服,拢拢头,然后从钱包里掏出几张大票,塞进我的手里,笑著说:「下次我过来的时候先给你传呼。」
我笑著点点钱,乐著说:「谢谢大哥了!每次都多给!下次您再来,一定给我打传呼,下次再来呀!」
我把张哥送走,一边点著钱,一边合计著怎么分配。然后又接了个彝族汉子,四十余岁,身高接近一米九,鸡巴很长,他又黑又高又瘦,还有些脏。我不喜欢他,但是他固执地要点我,他是客人,我只好接待他。他只喜欢一种姿势,让我站在房中间,他用胳膊抬起我的一条美腿,亮出屄眼,他让我搂住他的脖子,他抱着我,狠狠地挑射我。他的鸡巴很长,捅得我很酸很痛。我不喜欢这个脏家伙,于是生气道:「好痛啊,不来了!」但是那彝族汉子力气很大,被他紧紧抱住,挣脱不得,只好任他发泄。他一边操,还一边摸我的奶子,还要我设法站好,自己捧抱着二颗大奶,人不停的蠕动身体,整片臀部都是湿亮的汗汁。尽仅剩的一点力气紧紧夹紧肛门更使劲的打开腿缝,我女性的矜持早已被排山倒海的肉欲所淹没。我的陰核慢慢的变大从包皮中翘起而富有弹性,汉子知道时机已成熟,改以只手指轻轻的抠抚我的湿滑肉沟子。「很好!看妳怎么逃?毛在尿孔里!嘿嘿!」这会可真尽情的玩弄妈妈的尿道。彝族汉子用指甲去剥开尿孔,随手取个菜根,绕尖去碰触到尿孔更深的地方,尿道壁的嫩肉像鱼嘴一样的开合,接着热腾腾的淫汁加上骚尿一滴滴顺了菜根流出来滴在地上。「嗯…嗯…哦…哦… 」我抬着屁股迎合著,「啊哟……阿唷喂哦!」我激烈的挺腰哀吟,强烈的快感快速的麻痹敏感的身体,一阵昏晕,鬓髮全散卧倒在地。那种让人丧失神智的痒痒痛痛,令我的隂道不断抽稸啦,屄屁潮吹连连呀,可比死去还要痛苦羞愤啊!直到操了二十分钟,他射了,才放开我。以这个姿势被他操二十多分钟,我腰痛背酸,操完走都不稳啦。完事后,我快速的穿上衣服,飞奔医院。
……
自从上次见过阿毛后,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,这些天,我没日没夜的干,前前后后,吃足嫖客苦头,希望弄了点钱把丈夫送进了好点医院,生病的女儿我托付给了阿毛,阿毛把她送到了阿毛的姥姥家,我曾经去看过,那是个很好的老太太,我放心。可是丈夫的身体越来越不好,虽然进了医院,但我们只能住普通病房,丈夫咳嗽得越来越厉害,已经开始见红了,医生不只一次的严肃对我说,要我有个心理准备,因为他的肺气肿时间太长了,已经发生病变,估计可能是肺癌,最省钱的治疗也是每週两次的放化疗,钱太多了,已经上万,我支付不起呀!只能勉强在医院耗著,能让他多活一天都好。我到了医院,先是到住院处把这几天积攒的钱交给了会计,然后到食堂买了点吃的,送到丈夫的病房里,阿毛真的很好,特别交代了他手下的两个小混混在医院里守著。进了门,那两个小混混站起来,很规矩的叫了声『俞姐』然后就出去了。我看著满身插满管子的丈夫,子一,眼泪差点没掉出来。或许是丈夫有了心灵感应,他竟然睁开了眼,看到我,丈夫也一裂嘴,他想哭,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,只是干干的泣著。
我见他醒了,赶忙擦乾眼泪,小声的问他:「想吃点东西吗?」
丈夫闭上眼睛轻轻的摇摇头,然后又睁眼看著我,我坐在他身边,抓著他的手,一言不发的和他对视著,我们就这么静静的互相看著,一切都在眼神里表达出来。
外面的西北风又『呜呜』的刮了起来,彷彿是在悲,大风带来了雨雪,散落的雪花随著狂风漫天飞舞,城市的夜晚降临了,病房里很安静,彷彿时间凝固了,就在这城市被遗忘的角落里,有我,还有我的丈夫。
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,已是晚上7点。BP机响了起来,我赶忙去回电话。
「俞姐,我介绍了两个朋友到你那里去,一会见。」阿毛的话很简洁。
我放下电话,赶回四平门。阿毛热情的替我引见两个客人,一个姓张,张老闆,个子中等,30多岁,不胖,很有文化的样子,穿著时。另一个姓许,许老闆,个子比张老闆矮点,30多岁,胖乎乎的满面笑容,穿著讲究得体。
我送阿毛出去的时候,阿毛忽然小声对我说:「他们,捻子(钱)多,照到位了(伺候好了)。」
我点点头。
锁好门,我笑著对他们说:「两位老闆,别客气呀,坐呀。」
我一边说著,一边走到他们中间,慢慢的脱著衣服,许老闆很老道,笑著说:「大姐好爽朗哦!侍候我们,可得开放搞活哟!」
我笑著说:「咳,行!行!!您二位都是阿毛的朋友,不是外人,我也就不和您上俗套了,大家出来玩,不就是图个乐和吗?来,我帮您脱衣服。」
说完,我帮著张、许二人把衣服脱了,我仔细一看,两个人身上都是白白净净的,鸡巴也乾净,不大不小很适中,我拉著他们坐到床上,慢慢的捻著他们的鸡巴,笑著说:「噯呦!好大的货哦!许老闆,您的鸡巴真够个儿!」
他们二人的手在我身上乱摸著,许老闆乐呵呵的说:「大姐,别捧我!我识得的。」
我对张老闆笑著说:「哎呀!张老闆,您的鸡巴也不小呀!」说完,我对他们说:「说老实话!我干了这么多年,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个的鸡巴!又粗又长!一会操起来肯定带劲儿!」
张老闆和许老闆在我小手的擼弄下,鸡巴已逐渐挺起,我一边擼弄著鸡巴,一边让他们的手在我的乳房和浪上紧摸著,我一边有感觉的小声哼哼,一边浪浪的道:「我说,二位老闆,咱们谁先上?我这儿可刺痒著呢!要不,咱们开个洋荤,也学学老外,玩个三人行什么的……一个插浪屄,一个杵屁眼,然后,我再给您唆了唆了大鸡巴,让您美美的把精子射出来!怎么样?」
张老闆嘻嘻的笑了,对我说:「阿毛早就和我们说,大姐的人浪,活翘,今儿我们来,还就是为玩这个来的!来!」
张老闆和许老闆分别带好避孕套,张老闆躺在床上,我对著他挺起的鸡巴吐了口唾沫,用手猛擼了两下,然后跨到他的身上,鸡巴对准浪使劲坐了下去,张老闆舒服的哼出了声。
我将鸡巴连根坐进里,屁股前后小范围的伸缩著,转头对著许老闆的鸡巴吐唾沫,等鸡巴润滑了,我拉著鸡巴顶在屁眼上,许老闆骑在我的屁股上,慢慢的把鸡巴插进屁眼,等鸡巴都到位了,我忽然大声的哼了出来,『操!』张老闆和许老闆同时挺起屁股,一时间,房间里嘈杂起来……
「嘿!嘿!嘿!嘿!…」许老闆快速的前后运动著屁股,粗大的鸡巴在屁眼里抽插,黏糊糊的肛油加速了鸡巴的润滑,许老闆看著小屁眼被鸡巴操得乱翻,撒欢的插了起来。
「哎!哎!哎!哎!……」张老闆在下面一边使劲的揉弄著我的乳房,一边看著我浪浪的样子,大力的往上挺屁股,希里黏糊糊的淫液弄得他特别爽,张老闆激动的操著。
「发!……呀!……爷!……天!……哦!……啊!」我一边摇晃著头,一边胡乱的叫嚷著,前后夹击的刺激,让我头脑里一片空白,这活也真不是人干的。
『扑!』的一下,许老闆从屁眼里拔出鸡巴,鸡巴在空气中高挺了两下,许老闆呼呼的喘著粗气,一把把避孕套擼了下来,说:「好玄!屁眼太紧了!差点把套子搓破了。」
说完,许老闆用手指伸到我的屁眼里抠著,然后看著张老闆说:「你来玩玩这,油都出来了!」
张老闆一把把我推开,许老闆重新带上一个新的避孕套躺在床上,我跨在许老闆的身上,张老闆在后面插屁眼。
这个三人行足足玩了将近半小时,许老闆突然紧张的说:「我……我要来!躲开!」
说完,他大力的把我推到一边,张老闆也闪开,许老闆按住我的屁股,颤抖著手捏著鸡巴插进屁眼,然后玩命的使劲操著,屁股一下比一下快!
我知道他就快射精了,也急忙淫叫起来:「啊!啊!屁眼!啊!啊!屁眼破啦!我可憐的小屁眼被你捅破啦,喔,痛唷喔,裂開啦!啊!啊!」
在我一声声屁眼的乱叫声中,许老闆抽出鸡巴,快速的擼掉避孕套,我急忙起身含住他的鸡巴头,许老闆大叫一声「爽!」,鸡巴在我的小嘴里射出热热的精子!逼了我吞下了肚。
与此同时,张老闆赶忙将鸡巴塞进我的屁眼里抓紧操著,我刚刚嚥下许老闆的精液,再次大声的叫嚷起来:「噯呦!痛快!啊!啊!啊!啊!!」伴随著我最后一声淫叫,张老闆还没等把鸡巴抽出来就射精了,他死命的按著我的屁股,鸡巴插进屁眼里一动不动,我只觉得屁眼里的鸡巴扩大好几倍,一阵乱挺,火热的精子射了出来!
高潮以后,张老闆和许老闆穿好衣服,许老闆淫笑著对张老闆说:「你还是不行呀!还没抽出来就放炮了!」
张老闆也不甘示弱的说:「别管怎么说,我比你放炮放的晚,嘿嘿。」
两个男人互相打趣著。
我笑著伸出双手的大拇指说:「两位老闆都很强!很棒!操屁眼能操到这个程度的,就属您二位了!」
张老闆笑著说:「大姐,再怎么说,没有你这个小屁眼,我们也没这么爽!哈哈哈!」
我和许老闆也跟著笑起来。
许老闆站起来,从钱夹里拿出几张大票塞进我手里,乐呵呵的说:「下次还找你!嘿嘿。」
我点了一下钱,真不少!急忙浪浪的笑著说:「许老闆!看您说的!干嘛下次呀!这次不好吗?要不,咱们再点两炮?…」说完,我小声的对他们说:「哎呀!第一次,咱们玩的规矩,要是知道您二位是那么爽快的人儿,咱们玩点儿脏活儿,那才叫爽呢!」
张老闆眼睛一亮,淫笑著说:「什么活儿?」
我笑瞇瞇的说:「不带套子跑旱船,然后给您来个活叼,放炮以后,还给您用小嘴唆了个乾净……」
张老闆跃跃欲试就想上,许老闆一拽他,笑著对他说:「忘了!还有饭局呢!」
一句话提醒了张老闆,张老闆满脸惋惜的说:「算了,算了!下次再玩吧。」
我见没什么希望,转脸笑著说:「没关係,我还能跑了不成?早晚让您大爺爽個夠!」
张老闆和许老闆客气的笑了笑,向门外走去。
送走了他们,我穿好衣服,准备给自己弄点吃的,这时BP机又响了起来,我心说:阿毛真好,又有生意了。但是我的小屄卻抗議了,「吃不消啦,今天已經被姦了好幾回,酸酸痛痛,再也經不起折騰啦!」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丈夫已经整整昏迷两天了,医生把我叫出去,只对我说了一句话:准备准备吧,别到时候……后面的话我根本没听见。
连日的接客疲劳,我靠在丈夫的旁边昏昏的迷糊。
突然,我觉得有人碰我,我激灵一下坐了起来,只见丈夫竟然睁开眼,看著我,我急忙凑过去,小声的问:「饿吗?」丈夫摇摇头,我继续问:「渴吗?」
丈夫使劲的对我说:「咱女儿呢?我想看看。」
我装著笑,说:「快过年了,我把她送到一个姥姥那儿去了,那很好,有暖气,有好多好吃的,饿不著她……」下面的话,我实在编不出来了,眼泪几乎掉了下来。
丈夫的声音忽然清晰起来,他看看外面灰的天空,嘴里嘮叨著:「哦,快过年了……女儿别饿著……别冻著……过年了……快过年了……」
丈夫好像很睏,慢慢的闭上眼睛,突然,他又睁开眼,瞪大眼睛仔细的看著我,对我说:「哦,对了,还有个事儿,以后,不管怎么苦,你也别出去做了!好好照顾女儿,听我一句吧……」说完,丈夫缓缓的闭上眼睛,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,瞬间流了下来!丈夫就这么走了,撇下我……
过年了!大街上热闹起来,人们的脸上喜气洋洋,到处热闹非凡,电视里,电台里,到处是欢声笑语,鞭炮声,笑声,唱歌声,一片欢乐……
我还是穿著那身破旧的衣服,一瘸一拐的走在路边,慢慢的拐进了小胡同,慢慢的走进我那间破房子,屋里好冷呀!外面的天空还是那么混沌,灰灰的。
我和衣躺在床上,摸到了女儿的那个破旧的布娃娃,我把它抱在怀里,彷彿女儿在我的怀里,轻轻的拍著,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药瓶,颤抖著拧开盖子,把药片到进手心,一粒粒的放进嘴里,把那苦涩而冰冷的药片仔细的嚼碎,慢慢的嚥下去,心里想著:吃吧,吃吧,吃完以后,就能见到丈夫了,还有女儿……
啊!我好累哦,好困!我想好好的休息,好好的睡一觉,一觉醒来,没有了寒冷,没有了飢饿……我死死的抓著那个布娃娃……抱著它……
忽然间……
天空彷彿放亮……
大地一片明媚……一片广阔的天地……没有了飢饿……没有了寒冷……到处是绿茸茸的草地,到处是盛开的花朵……
我又看到了丈夫,他微笑著招呼著我,怀里抱著女儿……我扑向他们……紧紧的拥抱在一起……
跳呀!笑呀!……
跳呀!笑呀!……